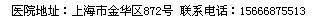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舌系带短缩 > 患病影响 > 绥德版聊斋志异之梦仙李道君
绥德版聊斋志异之梦仙李道君
梦仙李道君
文/李强国
李道君有其真名实姓,但知道他的大名没有几个人。他一生梦多,梦中遇到的人和事都在现实生活中再现。起初,人们都笑话他,以为他傻乎乎的只会胡说八道。后来,通过许多事实证明他没有说假话,因此,大家给他送了个梦仙李道君的绰号。
李道君是山湾村人,小时候体弱多病,瘦骨嶙峋,家里兄妹之中排行老二,乡人们见他皮包骨头脸色蜡黄,无精打采的样子,都叫他二猴。
邻人李长高家老婆七十岁那年,二猴随他的乸乸来串门,四个小脚老太婆盘腿在土炕上顶棍。二猴趴在一旁看她们玩纸牌,一会儿就困了,躺在炕旮旯里睡着了。
老太婆们玩得兴致正高时,睡醒后的二猴拉了拉李长高家老婆的衣角说:“二婶婶,我梦见你了。去年死了的老王家老婆刚才也坐在你的身边,看你们玩牌,她对你说了话,你自顾耍牌了,没有理她。她有点生气,沉下脸来,不紧不慢地对你说,明年冬月时她会接你来的,要你到她家里玩纸牌。她还说你架子大,平日里关系好好的,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怎么今天就成了冷冰冰的。说罢话就下了炕,走到门前又回过头来,狠狠地瞅了你几眼,然后扬长而去。”
李长高家老婆一听,面色突变,火冒三丈,扬起手就给二猴狠狠地搧了一巴掌。
耍纸牌的老太婆们都愣住了。
李长高排行老二,乡人们都喊他老婆是二老婆,说二老婆像个不讲理的蛮婆,左邻右舍的人都要让着她,厉害得没人敢招惹她。
二猴只是把他梦境中的事全盘托出,就招惹了她,她生气地训斥:“娃娃家懂个屁,净说些屁话,滚?屄远远家!”
二猴才六岁,哪敢跟凶巴巴的老太婆较个高低呢,一溜烟儿下了炕跑回家去了。晚上,他爷爷因为这件事又训了他一番。说他以后不要多嘴,世上有许多事心里明白,但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就会有是非。
过了几天,不长记性的二猴又随乸乸到二老婆家串门,趴在炕棱上,早把那件挨打受气的事抛在了一边,看她们用纸牌顶棍。
要知道,二猴和爷爷奶奶们生活在一起,小使小唤的事总是二猴,跑前跑后寻长递短,早上倒尿盆,给爷爷倒痰盂,晚上寻尿盆,扫炕扫地,站在灶圪崂双手拉风匣。大人不愿干的事,只要他力所能及,都乐意去做的。不过,他没有玩伴,也不去上学,像羊尾巴,整天跟在奶奶的身后,奶奶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二老婆也是个可怜人,男人走了好多年,有一个聋哑女儿,嫁人后不久也走了。不难想象,一个老人无依无靠,那日子孤苦伶仃的不可堪言,因此,大家包容地敬她三分,也让她三分。她实际上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可怜人,说话带锋芒,做事还是很厚道的。
二老婆见二猴又串门来了,不记仇,慌忙从门箱里拿出一个菜饼子擩给二猴吃,说自己老憨了,怎能下得了手打那六七岁的娃娃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显得极不自在,有愧疚感。
玩牌中,二老婆心神不宁,叹了口气说:“真是奇怪啊!昨晚自己也梦见王老婆了,她拉着我的手说,让我跟她去,到她那新宅一块儿玩纸牌,她已经搬新宅二年多了,你二老婆为啥不串来,还记得姐妹情分吗?我很生气,骂她死鬼。我跟你干什么去?跟着你做鬼去吗?她说那好,明年年底还来找你,那时就由不得你自己了。”她讲的梦中情节,大概和二猴之前说的一样样的。大家感到惊愕,谁也说不出其中的奥妙来。
第二年年末,家家忙着办年货,推碾子拉磨,营造米面,剪窗花,打扫卫生,准备辞旧迎新过大年,玩纸牌的那事就搁在一边了。
几天不见二老婆,邻居们都犯疑了,多次去敲二老婆家的门,窑里没有一点儿动静,于是找来宗亲,破门而入。只见二老婆面色蜡黄,身子僵硬,穿着崭新的寿衣,铺着寿褥,盖着寿被,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这事一传十十传百,一旦经乡人们的渲染,传的神乎其神,大家对二猴会作怪梦的事不可思议。
二猴十七岁那年,正是北风呼啸的大冬天,一大早起来,乘爷爷没有起床,他就烧了一锅热水,给多病的爷爷从上而下擦了一遍身子。爷爷起床后,又给爷爷理发剪指甲。比起往常,二猴变得更加勤快多事了。
上午吃饭的时候,家人们发现二猴的脸色不好看,显得样子十分沮丧,心也不在吃饭上。奶奶问他怎么了?他眼眶里满是泪水,说他梦见爷爷了,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再也不回来了。他的梦就是奇巧,没过了半月,爷爷真的走了。
这件离奇古怪的事也传开了,乡人们难免纷纷议论,都搞不清楚这二猴是个什么人。
大院里有个老先生,一生喜好斯斯文文,凡事经他口里出来,总会衍生出些枝枝丫丫来,那情节就会把人带入到故事当中。人称他是老员外,他也无缘于员外郎,仅仅是乡人们送给他的一个雅号。他默认了。有时也会在人前夸耀,自称员外,把他读过的书又讲给那些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人。他是个监生,出过远门,见过世面,别人不懂的事都来请教他。
有一次乡人们问员外,这二猴的梦为什么这么的奇怪?其实员外之前没有听说过这样奇特的事,他不知道其中的奥妙,但他还得想办法给人解惑。他一本正经地告诉乡人,别小看这小子,他有先知先觉的灵性,应该是传说中的梦仙吧!他肚子里有墨水,总能吐出些新鲜的词儿来。即便是杜撰的词儿来搪塞人,乡人们也乐意听,也信以为真。因此,后来人们不叫他二猴了,他已经是大人了,改口叫他梦仙,也不管他乐不乐意,乡人们都这样喊他,让他有了神仙的味儿。
二猴已是成年人了,他不愿听他们那些人给他谬赞的大名小号,但也管不住别人的嘴,只好管住自己的嘴,即便有怎样奇怪的梦,他再也不可将梦境中的事告诉他人了。
有一年的夏天,邻村有一位吴姓的年轻人得了一种怪病,平日里好好的,一旦犯病了,就会栽倒在地上抽风,缩成一团,不停地抖颤,两眼发直,有时口吐白沫,有几次把舌头都咬破了,家人们以为他中邪了。他们早知道山湾里有个梦仙的人,便来找他看病。
梦仙是庄户人家种地的子弟,从来不以江湖为生,本不给人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但出于善良的本能,又不能谢绝上门的客人。但他不行艺,不愿到人家家里去。那老吴只好把儿子带到梦仙家,也带了些果蔬作为见面礼,把希望寄托在梦仙的身上,但愿儿子早日康复,躲过这一劫。
梦仙让那吴姓的儿子躺在炕上,仰面朝天的放松身子,双目微闭,舌顶上腭,平心静气,什么也别想。吴姓儿子已被疾病折磨得脸色灰暗,不带一点儿喜色,当然对梦仙的话言听计从,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梦仙观察到吴姓儿子睡着后,自己就坐在一把椅子上,闭上双目,一会儿也进入了梦境。
在梦境里,梦仙只觉得自己像长了一双翅膀,可以展翅高飞,漫游开来。不知不觉中,他来到了山角中的墕口处,那是一户人家的居处,有三孔老土窑,倒座着一间草房,好像有人随着他,只是他也没有看到那个人的身影,只能听到那人的说话声。那人轻声地告诉他,这地方常有狐狸出没,深夜能听到狐狸的嗥叫,草房的大梁原是老土窑的顶梁柱,他们家的脑畔上的一角里埋着一个人的尸骸。说话之间,走出院外的坡下,便是一条通山大路,路下是一条深沟,沟底便是清粼粼的岩泉水,缓缓地流向前方,有三棵高大的柳树,其中一棵向对岸倾斜两米高处的躯干上寄生出一个圆球疙瘩来。这三棵柳树大约有两丈高,但枝条离路面还有一大段距离,路下是高崖石畔,有一条小径弯弯曲曲,通到了沟底,石崖下有人饮用的井水。
梦仙把他看到和听到的这一切都告诉了来人。那吴姓人一听惊得呆若木鸡。原来这山中小院正是他家的居所,他不明白梦仙怎么能知道这一切的,更加相信梦仙是高人,一定能治好自家儿子的病。
梦仙讲的一点也没错。这脑畔上埋的死人是吴姓人的母亲。原来吴姓人少年丧父,母亲改嫁他人,相继又生下了儿女。母亲死后,吴姓人召集了些宗亲把母亲的尸骸偷回来,埋葬在山中,倒腾过几次埋葬的地方,老是放心不下,担心后家弟妹们会像他那样把母亲偷回去,就把母亲又埋在自家脑畔上的土窑里。一旦有人来,院里的狗就会发声狂叫。
梦仙说,把你们的母亲和父亲合葬了,他们阳世早别,阴间也应该早会,这样才算入土为安。你的后家弟妹们早就原谅了你。他们的父亲将来也不会孤身,由他们的先母陪伴。其实,他们也知道母亲的遗愿,一旦撒手人寰,就一心想回到前夫那里去,或许这就是人常说的“头一碗好吃”的道理。他们理解母亲,也理解你的心思,但不能白白送给你,那样就会让别人笑话,说闲话。你偷你母亲我的事,他们一清二楚。他们私下也说了,这样也好,圆了大哥的梦,也实现了母亲生前的愿望。
现在好了,你回去就照我说的做,合葬父母后,你儿子的病自然就好了。
听了梦仙的话后,吴姓人连连作揖,千恩万谢地说了一气感恩的话。他很惭愧,没有将父母合葬,担心弟妹们来偷母亲,这种不合实际的提防心给自己儿子带来了癔病,是在给自己敲警钟,幸好今日梦仙指点迷津。冥冥之中,人的鬼魂不安时也会来作祟的。
他们回到家,请平师择吉卜地,筑了佳城,将父母合葬后,儿子再也没有犯病。
不过几年,梦仙也娶妻生子,和普通人一样过日子,敬上礼下,难免也要为生存而去奔波。
武家屯的武子彪在走西口的路上一往一返好几年了,和梦仙是好朋友,就攀梦仙走西口做皮毛生意。走了几趟后,梦仙也尝到了甜头,虽说是小生意,但比在家种地收入好多了,因此,他也一年四季走西口,成了倒买倒卖的小三行生意人。
有一年春季,梦仙住在镇川堡人申槐恩在郝刘滩开的小店里。夜深人静时,梦仙在梦中看到有一中年妇女在自己住的屋内像在自己的家中一样,做女工,做饭,清除杂土,忙忙碌碌总是停不下来,好像她看不见睡在炕上的人或者没有把梦仙视为客人,毫无羞耻感,自顾打理家务。而门缝里有两个人往屋内窥视,眼内流露出那种欲想进来而又不敢进来的忧郁目光。梦仙很惊讶这种梦中境遇。过了几日,这种场景在梦仙的梦境中反复了好几次。
这屋子里阴气盛,前些年,东川来此留宿的兄弟俩就住在这个屋里。三更时分,弟兄俩嚎啕大哭,好像死了亲妈的那样悲伤,惊起了侧房住的客人,大家连忙过来敲门喊叫,问他们为什么哭叫。兄弟俩止住哭声,迷迷糊糊地回答说,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他们根本就没有哭闹,而且睡得好好的。因此,都说这间屋里闹鬼,知道情况的人都不愿住这间阴森森的屋子。
又一天的夜里,深睡中的梦仙梦境中又出现了和之前相同的景象,妇人依然和之前一样忙碌着操持家务,门缝里的那两个人和往常一样向屋内窥视,忽然间,有话传入梦仙耳中,说他不该住在这里,坏了人家的好事,那两个人是妇人的男人和他的情人,男人姓丁,情人姓庞。梦仙住在这里,他们不敢进来,害得人家夫妻不能同床,情人不能幽会。
梦仙思忖再三,最终没有管住自己的嘴,把梦中的一切情况告诉了店小二。他醒悟到这屋子的地下有一个妇人的尸骸,之所以入此屋就宿的人常有异常现象,都是妇人作祟,不宜人居。
这话传到了店掌柜申槐恩的耳朵后,他相信了梦仙的话,几年以来,凡住入这间屋里的人,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怪事儿来,他思谋着要改造这间房子。
房子是土墙草椽盖顶,半天功夫就清理了土墙草木,接着清理地基。他让做工的人在地面上往下挖上二尺深地基,然后夯实。心里想的是想看看二尺以下有没有熟土,是不是下面真的有墓穴。
工人刚铲二尺深的土时,就发现了一团人的骨头,平铺在地面上,也没有个棺木,衣服都化为了尘土,说不准这也是个可怜的人,当年被人随意掩埋。申槐恩拿来一块红布,小心翼翼地把骸骨一节一节拾到红布上包裹起来,唯恐有遗漏。
为了平安,申槐恩请了一个小木匠,做了一口小棺材,又请阴阳选择墓地,将这无主的尸骸重新下葬,了却了自己心下不安的心愿。
经常和梦仙往来的小商贩,经常来住店的客人都知道这件事后,难免议论不休。有位老江湖的长者说,梦仙不是一般的人啊,他一定会下阴曹的。
梦仙本人,在走西口的路上,又有了新的名号,大家不叫他梦仙了,改叫他李道君了。
李道君后来出门走的更远了,也是为挣更多的钱,他经常和武子彪停留在花马池,灵州一带,收购一些滩羊皮,运回来卖给那些加工皮毛的小作坊。滩羊毛有九道弯,花形如同麦穗穗,裁缝出来的大氅都能卖个好价钱,因此,李道君愁的是买皮难,不愁羊皮卖不了。
有一次九月里,花马池遇会,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赶会,赶着牛车,拉着山货,都住在小店里。
九月里,已是农闲时了。当地的集会也叫丰收会,会期十五天。平日里,山里人一年也不进几次城,一到丰收会期,先卖山货,卖完山货后,就买办些日用品和年货,直到会末才陆陆续续往回赶。
九月九日那夜,李道君和武子彪住在一个店里同一房内,他们亲如兄弟,相互照应。谁知道睡到半夜,李道君口里嘟嘟囔囔不休,惊醒后的武子彪也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他身上的被子被掀在一边,光着身子斜躺在炕上。武子彪把被子盖在他身上,担心他着凉了生出病来。一会儿他又脚蹬手扬把被子掀在一边,好像在跟什么人说话似的,那动作像是在指天画地。因为武子彪熟知李道君,只能静静地观察也不敢叫醒他。
一会儿后,李道君闭着眼睛光着身子,径直走出门外到茅坑解了个手,又返身回房倒在炕上就又睡去了。跟在他身后的武子彪看到了这一切,虽熟悉情况但此时对李道君又徒生出几分陌生来。他的担心都是多余的,神使鬼差的李道君并不会因夜盲走路而碰碰撞撞伤了身子。在平日里,李道君私下会向他讲些阴曹地府的事,讲些形象古怪的魑魅魍魉,好像他是地府里的一个大官。他嘟嘟囔囔不休时,都是在睡梦中地府办事的表现。而躺在炕上的李道君,仍然在梦中呓语不止。
第二天一大早,店里的小商贩聚在小餐馆就餐,往常李道君只喝一碗米汤吃一盘炒面,可今天就不同平日了,李道君像三年没吃过饱饭的饿鬼,又喝了一碗米汤吃了一盘炒面。
大家笑话李道君的饭量今日翻了一番,真的让人不可思议。这时,武子彪拍了拍李道君的肚子说:“把饭吃到哪里去了?肚子还是扁扁的。”在一旁的马海飞笑着说:“你那饭一定是给鬼吃了,你是不是又下阴曹去来了?”
一旁的刘武义、刘扬、汪福才、三五、三锤、王胜等,大家你一言他一语,数落起李道君来。
武子彪把昨夜李道君身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毫不保留地告诉了大家后,大家便把李道君抬起来,拉腿的拉腿,拉手的拉手,抬在半空里,三锤将冷冰冰的手伸进了李道君的腋下,擩他的肚子,目的是让李道君讲讲昨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大家想听听他的异样。
李道君受不了大家的折腾,从地面上爬起来后,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只好把昨天晚上梦中的故事讲给大家。
子夜时分,我蹲在一个小土炕上,炕中心放着小炕桌,很陈旧了,桌面都裂开了缝,黑黝黝的,有几处露出被碰坑坎来。上面放着四个黑色的小菜碟。碟子里有下酒的菜。我也说不出来哪几个菜的名称。围在桌边的五个人有说有笑,显得很亲热,其实我并不认识他们,也不觉得陌生,只是他们的个头比我矮些。
这时,破门进来的是一位清瘦的小伙子,看上去二十多岁,蓝袄绿裤,来到炕前,急忙下跪,连连磕头,好像对着我说:“我是甘肃西峰人,遭遇荒年,来花马池投奔我的叔父。在一次鼠疫泛滥中,我命丧黄泉,但我在这里寄宿的日子里,邻家欺我叔父是外乡人,夺我叔父的宅基地,用铁锨把我叔父的头砍破。我叔父忍气吞声,斗不过地头蛇,也失去了宅基地。后因头伤不能痊愈,很快就撒手人寰。我已死了四十多年,从未离开这里,即便这些土墙草房二十年翻新一次,我还是留宿在你们住店家烧水房的柴炭垛上。”
他站起来后,把我们领到院子里说:“这院子过去不是这个样子。原来院中是一条大道,通过西侧的厕所那边一直往西去了,厕所是抢占了大路而挖的坑。北面是一排房,朝东有两间房。而你们住的这南侧房原是我家叔父的院子,被这袁老儒日的给抢占了。虽然我住在这里,吃喝拉撒都在这袁老儒日的家,依然是孤苦伶仃的,但我也找不到去处,也没个依靠,显得昏庸无能。”
“我一定要为我叔父报仇雪恨。我婶娘就住在南墙隔壁外,你们也认识,常喊他樊老婆。她也是个苦命人,小时候少吃没喝的,十六岁那年,因为窈窕秀气,被邻村财主家的花花公子看上了,托媒聘礼,很快约定婚期。结婚那天,土匪赶来劫婚,把她掳上山做了压寨夫人,都是长得漂亮惹的祸。没过二年,遇上了过路的队伍,杀了匪首,为民除害,她又跟着匪窝里的一个小伙子跑了。她为那个小伙子生下一双儿女后,因为好吃懒做,匪性不改,又抽大烟,据说又出去为非作歹,被人用乱石头给砸死了。后来,她嫁给了当地的一个老光棍,有了婆姨的老光棍,一下子变得勤快了,改掉了以往拖拖拉拉的惰性。”
“没过几年,老光棍年龄不小了,养家糊口拖累大,劳累过度成疾,也一命呜呼了。我叔父流浪到花马池,樊老婆收留了他,就这样磕磕绊绊凑合的过日子。”
“命不好的人,也遇不上好命运的人。我叔父也死的可怜,没有留下一男半女,和我一样,尸骨用破席片一卷,送到了沙漠里,成了流离失所的野鬼,也没有人来祭奠烧钱掛纸。”
“我不愿离开这里的原因是,我来到这里,我婶娘对我好,即便缺衣少食,她也没有嫌弃我。或许她命苦,甘愿接受苦难的咀嚼。”
“我没有什么要求,只想和你说说话。你看我这个可怜鬼,无亲无故的,流离失所,连个说话的伴都没有,鳏居多年,快要桎梏死了。”
“在我离开这里之前,我要做点厉害事,来报答我的婶娘樊老婆,报答她为我炊米补衣的恩德。”
“我是野鬼,是个十足的失魂落魄的野鬼,不会给人带来好运,你们就叫我恶鬼吧,我要给你们店里掌柜的一点颜色看看,让他们家的人不得安生,也不得好死,就是他们的子孙,我也要扣他一尿盆子污水。不过,这一切还早着呢,我婶娘离世后,我就开始行动,向他们作恶,即便我将来沦落到畜生道,我也心甘情愿。”
他伤心地哭诉了这一切后,又和我们回到了房里,向我们作揖施礼。恰恰到了鸡鸣时辰,他一下子就没了踪影。我也从深梦中醒了过来。
李道君讲了睡梦中发生的那些事后,大家没有享受到什么乐趣,反而心中徒生了些惊奇和不安。
多嘴的三锤闲话之中,把李道君梦中的事情全盘托出给了袁掌柜的老婆。
为此,袁老婆请李道君吃过几次饭,她心绪不宁,神色凄楚,想撬开李道君的嘴,即便她施尽浑身的解数,李道君只字不提梦中的事。据说,李道君向人讲述他梦中的怪异事后,就会头痛两三天。
这事儿在花马池传的纷纷扬扬,可以说大街小巷,山野村市无人不知。
后来传说,袁掌柜的店里经常闹鬼。之前南来北往的商客另择旅店,过去门庭若市的小旅店变得冷冷清清。无奈的袁掌柜只好忍痛割爱,低价将房转卖给他人。又听说那樊老婆死后,袁掌柜的疯了,光着身子四处乱跑,袁老婆也瘫痪了,袁家的儿子上吊死了,孙子被衙门家上了枷锁铐走了。袁家连连出事,像霜打了的茄子,蔫头耷脑的没了颜色。
从那之后,熙来攘往的村市集会上再也看不到李道君了。有的说他上了道观修炼去了,做了一名火居道士;有的说他隐居在终南山。至今,茶前饭后,人们还在津津乐道着李道君的那些传奇故事。
本文作者李强国先生近照
作者简介:李强国,男,陕西省绥德县张家砭镇五里湾村人,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乡下,农民,喜好诗文,有作品散见于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刊物及网络平台。兼好《易经》、宗教、民俗诸文化。现供职于合龙山道观,从事宗教、国学、心理学咨询及研究,偶有诗文面世。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