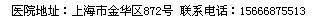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舌系带短缩 > 疾病检查 > 荒舌为什么夜里的人都哪儿去了
荒舌为什么夜里的人都哪儿去了
为什么夜里的人都哪儿去了
荒舌
让我们来找找满脑子病句的向晨吧。
夜幕扫地,会在他鞋帮上沙沙响地摩挲,使他总觉得自己被披着霓虹的杂人闲语穷追不舍。除了一双左躲右闪惯了的有如深窟的眼睛,毋须提及向晨的样貌,我想你该会后悔认出他来。
我只告诉你一人。向晨犯罪的兴趣可能没他自己说的那样简单地就消退了,我们还是警惕些好。每入夜,他定在某个行人周遭晃,如同丢了主的影子盼着附在谁的脚下;散漫的信步,失神的视线,皆是贪婪的吃相。餐厅里顾客遗落的手机、KTV前没上锁的山地自行车、低头族背包上的挂件……他迷恋于搜罗夜行人的碎屑,怀着普罗米修斯盗火时的心情,花上一整夜不让自己空手而归。可哪有偷窃时吟着诗歌就可以从轻处罚的道理呢?向晨不是好东西。
向晨向我坚称,那一夜他终于能够回答心中的疑惑,而不用再从别人人生的碎屑中寻求答案。说得我一头雾水。
大概是一个沾了陌生气味的夜晚,他的五脏六腑都找不到舒适的位置安放,只好不停摇晃。稀疏的夜行人的影子在马路上翻滚而偶尔相拥。街道两边的霓虹接连被夜风吹熄,棱角参差的楼房纷纷裹紧夜幕,冷漠地把行人踢到一边。
他的主人公出现了。一个皮肤没有血色的女人,遭遇了鬼打墙似的一直扶着墙一步步向前跌去。她很可能在哭。向晨注意到她,是因为他瞥见有一小块泪滴般的闪光从她身上剥落。分明隔着一条大马路,他却清楚地听见那闪亮东西坠地时的叮咛,宛若一滴冰水将心窝砸得酥麻。待她走出约三十步后,向晨雀跃地横穿马路,从地上拾起一把钥匙。直觉驱使他快步跟上那个女人。
她的家。对。与世界隔绝甚远的未知空间。是的,是我的了。向晨愉快地想着,每一步都像跨过自家门槛那样闲适。
所以主人公的名字呢?该不会是你杜撰的吧?我不耐烦地打断向晨的絮语。名字不重要!你会知道的,他忿然答道。
倘若向晨没有了这样糟糕的兴趣,不难想象那会是一种美丽新世界的“伊普西龙式”的生活在等着他。向晨的工作是在一间小工作室里“烧玻璃”。他的公寓在工作室楼上,一日三餐则在两者楼下解决。他本该是沙漏中的沙粒,天亮了倒过来,天黑了倒回去,只能隔着该死的玻璃在脑子里描摹四散尘埃的轨迹。
向晨屋子里堆满了我欣赏不来的玻璃“艺术品”,每一件都莫如将一幅幅油画拧扭起来再定形的堆砌物,没有一丝玻璃应有的通透性,取而代之的是浓厚忧郁的色块。都是些卖不出去的非卖品,他说。难怪他的同事天天叫他“艺术家”他也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了。
除此之外,他屋子里挤满了别人的东西。耳坠、宽边帽、用胶带补好的相册……去他家宛若造访地精洞穴,里面满是丧命旅人的遗物。对向晨而言这些也一样,它们的主人只在他的屋子里活命一个晚上,天亮即死去。作为他那已死的玻璃艺术的偿命鬼,他开始乐衷于弄文舞墨。三更半夜,他自制的玻璃灯罩让炽热的光芒蘸上沉闷的色彩,整个郁思稠结的屋子变得黏糊糊,他倚仗着“碎屑”断断续续地下笔,杜撰些乏善可陈的他人人生。自己缺少,就从别处拿,是这样吧?他曾给我看一两篇,其中字迹之乱、病句之多,让我忍不住摩挲纸面,仿佛能找到一根黑线头,一扯尽,这些文本就还原成了白纸。我指出有一句“为什么夜里的人都哪儿去了”有毛病,他立马提笔在“夜”之前添了问号。“簸箕里酿不出酒来。”——作为他的后辈,我这样评价似乎太狂妄了。
可没办法,他始终是隔着玻璃看人的。
向晨又开始杜撰他的午夜了。他的午夜总是那么沉寂,只有飞蛾猛击路灯的冷淡声响异常清晰。久久会有车路过,他尝尝忍不住与晃眼车灯后模糊的人影蓦然对视。
钥匙的主人进了她的公寓,向晨则兴冲冲地向另一单元的大门跑去。动态感应廊灯被她挨个点亮,在对面单元望去,整栋公寓酷似条形码;但她又走得太慢了,先前点亮的灯又会熄灭,一条巨型贪吃蛇在夜幕下蠕动。蛇被截短了。他知道钥匙对应着哪扇门了。
钥匙的主人翻了翻口袋和包包,一无所获,继而像踩点的小偷在门前晃啊晃。她显然没有备用钥匙。向晨觉得她止住哭了。她掏出手机,打给……谁?物业早下班了;有要好的友人吗?她把手机扔回了包里。这时向晨不相干地想起惯常买的抽纸升价了五毛。他忽然发觉自己有些近视,像隔着一小块毛玻璃——真像隔了块不可逾越的玻璃,他暗忖,她一次也没有向对面的自己注意过来。他把自己当作她的某个像这样相瞻已久的邻居。她貌似决定敲敲邻居的门,却浑身哆嗦一下脱力了,全身无力地委门滑下,直至溜出他的视野。
不妙!警觉烧穿了头皮,向晨发疯似的奔跑,在楼梯间飞旋下坠,迅速把这个公寓内的“牛皮藓”小广告尽数刨尽。顾不上渗出血丝的指甲缝,他在一沓烂纸里挑拣一串串数字,打出一通通电话。手机屏幕沾了些血,他终于打通了。
焦虑的释怀几乎令他喜极而泣,连舔自己受伤的脏指头都觉得甜。要是他再不走运些,或那女人警惕性更高一些,钥匙可能就报废了。他料想她会换一把锁,就必要先于她找到一个锁匠。现在他走运了,因为那老师傅打麻将到深夜。
向晨迫不及待地挤进夜幕,开始杜撰一次刻意的邂逅。
不得不说向晨总是在动坏脑筋。
在我参加完初中同学聚会的那个晚上,这个二十来岁、眼角下垂的男人突然从我背后找上我,要借手机打个电话。好在我疑心较重,他每挪一寸我就走进一步,没得机会。半晌,他谢都没道便走了。他用我手机打给同个号码两次,都没通。我某天不小心打出过一次,竟尴尬地发现这号码就是向晨自己的。我们便是如此相识的,巧合得令我后怕。
噢,我不该打断的。但向晨并不在意。
苍白的廊灯在喘息似的频闪,光暗极速地交替如同凭空生出雾霭。她闭上灼痛的双眼,劫难开端的记忆立刻涌现眼前;一睁开眼,她又回到了劫难的结尾。
朱琦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觉得自己真如同事们叫她的“猪猪”一样蠢得像猪。
她从包里翻出一沓崭新的钞票,开始数,数完又倒着数回去——回去!要是数着数着,它们全从指缝溜回当铺的钱匣子里该多好!可不多不少,一千六百一十整。接着回去中午跟经理请半天假的时候,好好吃顿午饭;和女友许久未见了,哪怕忘了吃饭也要好好打扮。再回去她和女友见面的那一刻,先让女友好好把话说清楚,让自己能像个大人、心平气和地……而不是一见面就要女友夸自己戴上了那条项链。那是女友送给她的项链,她连配套的容纳袋也珍藏着,现在不在了,她却每分每秒都觉得它在脖子上紧紧勒着。如此炽热,让她无法呼吸。怎么才能回得去呢?朱琦在最不幸的日子里腹背受敌,连抛开一切倒头大睡都做不到。
灯灭了,因为她不再动弹。灯忽而闪亮,那是一个男人踱来。
朱琦匆匆往包里塞好钱,抹抹脸吸鼻子,好不容易才站起来。她和所有邻居都不熟悉。刚想逃窜,不料男人突兀地朝陌生且可疑的自己问道:“有什么,邻居能帮得上忙的吗?”
“没有……”她再三放松抽搐了半天的嗓子,勉强答道:“谢谢。钥匙丢了而已。”
“哦哦。”男人的声音过于清晰,灌进她耳中却像极了责骂:“真不巧,我刚在开锁铺那里路过,早收摊了。物业也下班了啊。你有地方去吗?都凌晨了。”
一张口她就有种反驳的冲动,但最后还是抿着嘴唇,无奈地说:“抱歉,先走了。”她还不清楚处境有多糟吗?感情或自家,以往在夜里感到无助时她就往这两扇门钻,如今都已紧闭,把她关进幽闭的城市里。她只是不想被人说明。别人说的话太真实了,像水族馆里的鱼总比海底大江里的清楚得多。
“哎等等!我看你今天是伤心个够了,眼哭得跟炒板栗似的。我也有一肚子脏水啊,你当作补点水分听听吧!”
她还没听明白男人在喊什么,男人就不容置喙地发起牢骚,对着黑灯瞎火的万家窗户情绪激昂地“演讲”,仿佛所有人趁夜串通一气仅为他编了弥天大谎,于是他有义务去指责、去揭发似的。一开始男人好像在讲大学学的艺术到现在成了垃圾,因此书就白读了;后来的话她有一句没一句地听也听不懂。像什么“该被打磨的同事”、“苹果从糖心腐烂”之类难懂的语句被她礼貌地忽略,没让一丝尴尬阻挠他发声。当他讲到为抽纸涨价感到极度烦躁的原因是他不知该不该换个品牌时,朱琦悄悄打了个嗝。可她又没想到,这个戾气浓重的糟糕男人被她正眼注视时却会弄丢尖牙利嘴,学生似的腼腆地别过脸、亲吻晦暗。“我的全部都让你听去了……不说点你的我岂不是超不划算?”
她嘴还没张开,声音就掉出来了。她讶异于自己能随便到这种地步:深夜、外面、男人、劫难,喝醉了似的颠三倒四。
每次朱琦谈起只为女友开辟的情感世界,一种几近亵渎神明的满足感有如皎月显现。她能看见耶和华从亚当身上摘下第一根肋骨,然后第二根,这时亚当就已经死了,而他的肋骨正缓缓化成两人……她和许多人讲过开头,而只有这个男人听了结尾。女友与她告别,理由是喜欢男人。她失去理智,硬拽着女友到一家简陋的典当行里把珍贵的项链当成了一千六百一十。“想拿回去就自己用钱赎吧!”朱琦说了这种话,以为是说来气女友的,最后却发觉是说给十几个小时后的自己伤心的。女友都走了,话还能说给谁听呢?“猪……”暗暗骂着自己。
“那好,我们去拿回来。”男人带着笑意说道。“女朋友可真是难找。”
朱琦摇着头,可此刻谁都希望玩笑话能够成真。
清净了。暗夜的清净并不是安分的,在单薄的卷闸门与宿醉的管道间来回弹跳。你能听出来它的质量、形状,以及雀跃的心。空荡荡的街道上只有安分的红绿灯单调地打黄灯。
几分钟后他们造访了一座古旧的公寓。那里面所有配套的房门上部分都有个翻窗。好运气让美梦更近了。男人随身带着锉刀,他攀上当铺的后门,先取下一块玻璃再伸手进去把阻碍的锈铁条磨断,朱琦则忐忑地接过递下来的玻璃、铁条……男人钻了进去,后门开了。尽管铺主不住这里,他们也屏息凝气。正当她凭记忆从柜台下抽出那粉色的丝绸袋子时,一声犬吠仿佛将他们的骨头嚼成了细屑,她一急就把手里攥着的一千六百一十狠狠砸在狗脸上,钞票哗哗地纷飞像海里的沙丁鱼群。
是心脏长了腿在奔跑,她感到全身空洞洞的。脑子里满是自己被撕咬得血肉模糊后被居民逮住的场景,仿佛他们奔逃的身影不过是绝望的幻想。随着心跳打蹦,每次落地都是一次无比快意的鸣掌。男人说:“我看看。”她便递去粉袋,然而男人从里面攫出的,是那把闪亮且一生只闪亮这么一次的钥匙。朱琦失神地碎碎念着:“猪……蠢猪啊我。”
就假设它在包包里游走,偶尔掉在了收纳袋里吧。
“我肯定要请你喝杯茶……”天快亮了不是吗?
向晨在几个小时内想象过无数次,他要装作一个死于白天的幽灵,在这里从容地数衣服挂钩的数目,或挑拣些与这里格格不入的物件带走。
“我家,超乱的。”朱琦给他泡上一包红茶后洗澡去了。
水声滴滴答答。他疲惫地躺上沙发,怎么也睡不着。不偷?偷吗?偷什么?他握着口袋里的复制钥匙思考,发觉什么东西都没了意思。早晨一来,他又得赶去工作室。踏过夜昼的交界才察觉二者并无区别。
水声止住了,人却没出来。向晨听得见朱琦的啜泣,他太熟悉了。他昏沉地翻了个身。有什么意思呢?一切都像寄出一张明信片,辗转异国荒域,最后却捎回自己手里一样,除了疲乏什么也没有。
天亮了,恍若四下无人,她不再出来了。向晨猛地发觉,自己并没有隔着玻璃观望她,她是蚀刻在玻璃里边的。绕过玻璃看,后面空无一物。
“我想,我知道为什么了,知道夜里的人都哪儿去了。”
“一大早打电话来折腾我就为了讲这个?不知道我是高三狗吗?”我哭笑不得,说到底我跟向晨又不是很熟,于是挂了。
夜行人总是难懂的,不是吗?但或许黑夜能够给我一个不挂断电话的理由继续去了解他。我们都在等夜幕从天边扫下。
图片
网络
编辑
一介民女
大家语文感谢赞赏支持,点赞转发也极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