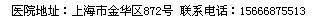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舌系带短缩 > 疾病检查 > 连载丨赫尔曼黑塞悉达多4
连载丨赫尔曼黑塞悉达多4
赫尔曼·黑塞(HermannHesse,-),德国作家、诗人、评论家,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以《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的彷徨少年时》、《荒原狼》、《悉达多》、《玻璃球游戏》等作品享誉世界文坛。年46岁入瑞士籍。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轮回
席特哈尔塔过了很长时间的世俗生活和性爱生活,却并没有完全属于它。他在狂热的沙门年代里扼杀的性欲又苏醒了,他尝到了财富的滋味,尝到了肉欲的滋味,尝到了权势的滋味,但他心里很长时间仍是个沙门,而聪明的卡玛拉也准确地看清了这一点。仍然是思考、等待和斋戒的艺术引导着他的生活,他对世俗的人们,对那些孩子般的俗人依然生疏,正像他们也不熟悉他一样。
岁月荏苒,席特哈尔塔置身在安乐中几乎没觉察年华的流逝。他富了,早就拥有了一幢自己的住宅以及自己的仆人,在城郊的河边还另有一个花园。人们都喜欢他,需要钱或忠告时就来找他,可是除了卡玛拉,没有人跟他特别亲近。
他以前在青春年代里体验过的那种高度敏锐的清醒,在听戈塔马讲经之后的日子里,在与戈文达分手后的日子里,他体验过的那种高度敏锐的清醒,那种紧张的期待,那种既无学说又无师长的值得自豪的独立,那种准备在自己内心倾听神灵声音的灵活决心,都渐渐变成了回忆,变成了过去;原来离他很近的在他心中流过的圣泉,已经是在远处轻轻地流淌了。他向沙门学到的许多东西,他向戈塔马学到的许多东西,他向婆罗门父亲学到的许多东西,依然长时间地留在他心里:节俭的生活,思考的乐趣,潜修的光阴,还有对自己,即对那个既非肉体又非意识的永恒自我的悄然认知。它们有的确实还留在他心里,但是,毕竟已一个接一个地消失,被尘土掩盖了。就像制陶工匠的圆盘,一旦转动起来就会久久地转个不停,最后才慢慢地减速和停止那样,席特哈尔塔心里的苦修之轮、思考之轮和分辨之轮也是这样久久地转动不已,现在仍在转动,但是已经慢了,晃动了,接近停止了。就像温气渗入正在枯死的树干,慢慢地充满了它并使之腐朽那样,俗气和惰性也侵入了席特哈尔塔的心灵,慢慢地充满了它并使之学生,使之疲乏,使之麻木。而他的情欲却变得活跃起来,学到了很多,也体验了很多。
席特哈尔塔学会了做生意,学会了对人们行使权力,学会了与女人寻欢作乐。他学会了穿华衣美服,使唤奴仆,在香气袭人的水里洗澡。他学会了享用精心烹调的饭菜,烹用鸡鸭鱼肉、调味品和甜点、饮用使人懒散、健忘的酒。他学会了掷骰子、下棋、看舞蹈、坐轿子和睡软床。但是,他仍然和别人不一样,他感到自己比他们优越,看他们时总是略带嘲讽,略带揶揄的轻蔑,这正是沙门对俗人始终怀有的那种轻蔑。每当卡马斯瓦密身体不舒服,生气发怒,感到受了侮辱,受商人的种种烦恼困扰时,席特哈尔塔总是怀着嘲讽袖手旁观。不过,随着收获季节和雨季过去,他的嘲讽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减弱了,他的优越感也有所收敛。随着他的财富日益增长,席特哈尔塔本人也染上了那种孩子般俗人的一些特点,染上了他们的孩子气和谨小慎微。而且,他羡慕他们,他跟他们越相像,就越羡慕他们。而他羡慕的正是他自己缺乏而他们却拥有的东西,那就是他们能使他们的生活显得十分重要,他们对欢乐与恐怕的激情,以及他们演变的不安而又甜蜜的幸福。这些人不断地迷恋自己,迷恋女人,迷恋他们的孩子,迷恋名或利,迷恋种种计划或希望。但是有一占他不是向他们学到的,那就是孩子般的快乐和孩子般的愚蠢;他向他们学到的恰恰是他自己很瞧不起的讨厌东西。于是,越来越多地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在参加了一个欢乐的晚会之后早上迟迟不起床,感到昏头昏脑和十分困乏。当卡马斯瓦密诉说自己的烦恼而使他感到无聊时,他往往生气发怒和烦躁不安。他掷骰子赌输了钱,就十分过分地放声大笑。他的脸仍然比别聪明和精神,但是他笑得少了,接连出现那些只是在有钱人脸上常见的特点,那种不知足、病态、厌烦、懒散和冷酷无情的特点。有钱人的心理疾患慢慢地俘虏了他。
疲乏就像一道纱幕,一层薄薄的雾气,慢慢地降临到席特哈尔塔身上,每天都变厚一点,每月都变混一点,每年都变重一点。就像一件新衣随着时间变旧,随着时间失去鲜艳的色彩,出现斑点,出现皱褶,衣边磨损,有些地方开始出现破绽那样,席特哈尔塔与戈文达分手后开始的新年生活也变旧了,随着流逝的岁月失去了色彩与光泽,积满了皱褶和斑点,失望和厌恶已然产生,藏在心底,有时已经丑恶地露了出来。席特哈尔塔没有察觉。他只是发现,自己内心那种响亮的胸有成竹的声音,那种曾经在他心里苏醒并且在他的光辉岁月里时时引导他的声音,如今变得悄然沉默了。
世俗俘虏了他,还有享乐、好色和懒散,最后是他始终认为愚蠢透顶的最瞧不起并加以讥诮的恶习——贪婪。财产、家业和富有最终也俘虏了他,对于他不再是游戏和小玩艺,而是变成了锁链和负担。席特哈尔塔是通过一条不寻常的奸诈途径,也就是通过掷骰子赌博,陷入这最后、最可耻的歧途的。从他心里不愿再当沙门的时候起,席特哈尔塔就开始了旨在赢钱赢珠宝的赌博。往常,他只是当作庸人的习俗笑着漫不经心地参与,如今,他玩起来赌瘾越来越大了。他是个令人生畏的赌徒,一般人不大敢跟他赌,因为他下赌注时特别多特别狠。他进行赌博是出于内心的困境,输掉花光那些讨厌的金钱使他得到一种发怒式的快乐,而用别的方式他就不能对商人奉为偶像的财富表示出更清楚更尖刻的蔑视。因此,他毫不可惜地押大注,憎恨自己,嘲讽自己,一赢千金,又千金一掷,输掉钱,输掉首饰,输掉别墅,然后再赢回来,又输掉。他喜欢那种恐怕,那种赌博中因为押上了大注而提心吊担时感到的恐惧,那种可怕的令人窒息的恐惧,并且努力使这种恐惧不断重现,不断增强,被刺激得越来越强,因为只有在这种感觉中他才多少有点儿幸福,有点儿陶醉,在他那百无聊赖的、温吞吞的、单调乏味的生活当中才多少有点儿心安理得。在每一次大输之后,他都设法积累新年的财富,更热心地做买卖,更严厉地逼迫债户还帐,因为他要继续赌,继续挥霍,继续对财富表示他的轻蔑。席特哈尔塔在输钱时失去了从容镇定,对拖欠的债户失去了耐心,对乞丐失去了同情,对施舍失去了兴趣,也不再借钱给求贷者。他在豪赌中可以一掷万金并且付之一笑,可是做起生意却越发严厉,越发小气,夜里做梦有时也梦到钱!他常常从这种可憎的迷醉中醒来,常常从卧室墙上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脸变老变丑了,羞愧和恶心常常袭扰他,于是他继续逃避,逃到新的赌博之中,逃到肉欲和酗酒的麻醉之中,再从那儿回到攒钱和赚钱的本能之中。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循环中他疲于奔命,日渐衰老,病魔缠身。
这时,一个梦提醒了他。那天晚间,他在卡玛拉那儿,在她那美丽的大花园里。他们俩坐在树下交谈,卡玛拉说了些引人深思的话,话背后隐含着某种悲伤和倦乏。她请求他讲述戈塔马,而且老是听不够,戈塔马的眼睛如何纯洁,他的嘴如何文静优美,他的笑容如何亲切,他的步态如何平稳。他不得不把这个活佛的事儿向她讲了好久,然后卡玛拉叹了口气,说道:“将来,或许要不了多久,我也会去追随这位活佛。我要把我的大花园送给他,信奉他的学说。”可是接着,她又挑逗他,在爱情游戏中怀着痛苦的热情箍紧他,咬他,淌着泪,仿佛要从这空虚而短暂的情欲中再一次挤出最后一滴甜蜜来。席特哈尔塔忽然明白了,淫欲和死亡是多么接受。然后,他躺在她身边,卡玛拉的脸紧挨着他,从她的眼睛下面和嘴角旁边,他清晰地读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文字,一种由细线和浅纹构成的文字,让人联想到秋天与老年,就像席特哈尔塔自己,年方四十,黑发间却已经出现了花白的头发。在卡玛拉俊俏的脸上记得写着疲倦,疲倦和业已开始的憔悴,以及有意掩饰的、还没有说出的、也许还没有意识到的不安:害怕衰老,害怕秋天,害怕不可避免的死亡。他叹息着向她告别,心里充满了不快,充满了隐秘的不安。
然后,席特哈尔塔回到自己家里和舞女们饮酒消磨长夜,对与他同等地位的人摆出轻蔑的样子,其实他已经没什么可自负的了。他喝了好多酒,午夜之后很晚才摸上床,虽然疲倦却很激动,真想大哭,几乎绝望,想睡而又久不成寐,心里充满了一种他以为无法再忍受的愁苦,充满了一种他感到浑身难受的恶主,就像酒的那种温吞吞的讨厌味道,就像过分甜腻而单调的音乐,就像舞女们那过分柔媚的笑容,就像她们的秀发和乳房那过分甜腻的芳香。但是,最让他恶心的是他自己,是他的香气扑鼻的头发,是他嘴里的酒味,是他的皮肤的疲沓与不适。就好像一个人吃得太多或者喝得太多,难受得呕吐出来,然后由于一身轻松而感到高兴那样,这个失眠者也希望能在一阵呕吐之后摆脱这些享乐,摆脱这些习惯,摆脱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摆脱自己。直到天光大亮,他的住所门前大街上开始了喧闹忙碌时,他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陷入一种半麻木的状态,一种睡意蒙笼。就在这片刻之中他做了一个梦。
卡玛拉养了一只奇异的小鸟,关在一个金鸟笼里。他梦见了这只小鸟。他梦见这只鸟儿变哑巴了,而平时早上它总是鸣啭不已。他发现了这点,就走到鸟笼前往里瞅,小鸟已经死了,直挺挺地躺在笼子底。他取出死鸟,在手里掂了掂,就把它扔了,扔到街上。他感到很害怕,心里很难受,就好像他把一切价值和一切美好都跟这只死鸟一起扔掉了。
从这个梦中惊醒后,他感到自己被深沉的悲哀包围着。毫无价值,他觉得自己过的生活真是既无价值又无意义,并没有留下什么生动的东西,也没有留下珍贵的或者值得保存的东西。他孑然孤立,空落落的,就像岸边的一只破船。
席特哈尔塔阴郁地走进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花园,锁好小门,坐到一棵芒果树下,感受到心中的死亡和胸中的恐惧。他坐在那儿感受到了自己心中如何在衰亡,如何在枯萎,如何在完结。他渐渐地集中了心思,在脑子里再一次回顾了他这辈子走过的路,从他能够想起的最早的日子开始。他什么时候曾体验到一种幸福,感受到一种真正的狂喜呢?噢,对,他也有过好几次这样的经历。在少年时代他就品味过这种欢乐,当他受到婆罗门夸奖时,当他远远超过同龄人,在背诵诗书、与学才辩论以及当祭祀助手都表现得出类拔萃时。那时他心里就感觉到:“一条路摆在你面前,你的使命就是走这条路,神灵在等着你。”到了青年时代,思索的目标不断向上,这使得他从一大群有同样追求的人当中脱颖而出。他在痛苦中思索婆罗门的真谛,每次得到的真知都只是在他心里激起新的渴求,而在渴求当中,在痛苦当中,他又总是听到这个声音:“继续!向前!这就是对你的召唤!!当他离开故乡,选择沙门生活时听见了这声音;当他离开沙门,投奔那位活佛时听见了这声音;当他离开活佛,走进昏沌之中时还是听到了这声音。他已有多久没听见这声音了?他已有多久没有再攀上高峰了?他走过的路是多么平坦和荒凉!好多个漫长的年头,没有崇高的目标,没有渴求,没有提高,满足于小小的欢娱,却又从来没有知足过!这些年,他一直努力和渴望成为一个跟许多人同样的人,跟那些孩子同样的人,可是他自己却不知道,他的生活比他们远为不幸和可怜,因为他们的目标跟也不同,他们的忧虑也跟他不同。像卡马斯瓦密这类人的整个世界对于他只是一场游戏,一场供人观赏的舞蹈,一场悲剧。只有卡玛拉是他真心喜爱的,是他珍惜的——但她还是那样吗?他还需要她呈,还是她需要他?他们不也是在玩一场没完没了的游戏?为这个而活着可有必要?不,没有必要!这游戏叫轮回,是一种儿童玩的游戏,玩起来也许很有趣,一遍,两遍,十遍——可是,就永远这样玩下去么?
这时席特哈尔塔已明白,这游戏已玩到了头,他不能再玩下去了。一阵寒战传遍他全身,他感觉到,内心深处有什么死去了。
那天,他一直坐在芒果树下,思念他父亲,思念戈文达,思念戈塔马。要做个卡马斯瓦密就必须离开他们吗?夜色降临时他依然静坐不动。他抬头仰望星星,心想:“我坐在我的芒果树下,坐在我的大花园里。”他微微一笑——他拥有一棵芒果树,拥有一个大花园,可是这有必要吗?这对头吗?这不也是一场愚蠢的游戏吗?
就连这他也要彻底了结,就连这也在他心中死去了。他站起来,向芒果树告别,向大花园告别。因为他一整天没有进食,他感到饥肠辘辘,想起自己在城里的住宅,想起自己的卧室和床铺,想起摆满了佳肴的餐桌。他疲乏地笑笑,摇摇头,告别了这些东西。
就在当天夜里,席特哈尔塔离开了他的花园,离开了这座城市,再也没有回去。卡马斯瓦密派人找了他很久,以为他落入了强盗之手。卡玛拉没有让人找他。她得知席特哈尔塔失踪时并没有惊讶。她不是一直在盼着这个消息么?原来他不就是一个沙门,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个朝圣者么?在最后那次欢聚时她感受得尤为深刻。她在失败的痛楚中寻欢作乐,最后一次把他紧紧地贴在心口上,再一次感到自己被他完全占有了。
当她得知席特哈尔塔失踪的第一个消息时,她走到窗前,走到羊着一只罕见的小啼鸟的金鸟笼前。她打开笼门,取出小鸟,放它飞走。她久久地目送着那只高翔的鸟儿远去。从这天起,她不再接待客人,关闭了自己的住房。过了一段时间后她意外地发觉,跟席特哈尔塔的最后一次欢聚竟使她怀了孕。
在河边
席特哈尔塔在森林里游荡,离开那个城市已经很远了。他只知道他不会再回来,他多年来所过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尝够了这种生活的滋味,已经到了恶心的地步。他梦见过的那只鸣鸟死了,他心中的鸟儿也死了。他深深地纠缠于轮回之中,已经从各方面尝够了厌恶和死亡的滋味。就好像一块海绵吸饱了水。他满怀厌恶,满怀愁闷,满怀死亡之感,世界再没有什么能吸引他,使他高兴,安慰他了。
他热切地希望能忘却自己,得到安宁,干脆死掉。但愿来个闪电,劈死他!但愿来一只猛虎,吃掉他!但愿有一杯酒,一杯毒酒,使得他麻木、忘却和沉睡,永远不再醒来!还有哪一种污秽他没有沾染过,还有哪一种罪孽和蠢行他没有干过,还有哪一种心灵的空虚他没有承受过?他还有可能再活下去么?还有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吸气和呼气,感觉到肚子饿,重又进餐,再去睡觉,去和女人睡觉么?这种循环对于他来说不是已经精疲力竭并且结束了么?
席特哈尔塔来到森林中的一条大河边,这正是当年他年轻时从戈塔马那个城里出来,一个船夫为他摆渡的那条河。他在河边停下,犹豫不决地站在河岸上。疲劳和饥饿已经使得他虚弱不堪,他干吗还继续走呢?他前往何处,奔什么目标呢?不,已经没有目标了,只有这种深深的痛苦的渴望:甩掉这乱七八糟的梦境,吐掉这变了味的酒,结束这糟糕的可耻的生活!
从河岸上探出一棵树,弯着伸向河面,那是一棵椰子树。席特哈尔塔让肩膀靠在树干上,用一只胳臂搂住树干,俯视着身下流过的碧绿的河水。他往下看,感到心中涌动着这个愿望:松开手,让自己沉溺到水里去。从水中映也一种可怕的空虚,而他心中的可怕的空虚则与之呼应。是的,他要完蛋了。留给他的出路就是毁灭自己,砸烂自己生活的失败产物,丢弃它,把它丢到幸灾乐祸的神灵脚下。为正是他所渴望的巨大突破:死亡,毁掉他所憎恶的形体!但愿水中的鱼把他吃掉,把席特哈尔塔这条狗、这个疯子、这个腐朽的身躯、这颗衰微和滥用了的灵魂吃掉!但愿鱼类和鳄鱼把他吃掉,但愿恶魔把他撕成碎片!
他面容扭曲地呆望着水面,看见了映出的那张脸,便朝它吐口水。他疲惫不堪,让胳臂松开树干,轻了一下身子,以便垂直地落进水中,最终葬身水底。他沉下去,闭着眼睛,迎向死亡。
这时,从他心灵深处的偏僻角落里,从他这疲倦一生的历历往事中,传来了一个声音。那是一个字,一个音节,他不假思索就喃喃地念了出来。那正是所有婆罗门在祈祷的开头和结尾时都用的古字,那个神圣的“唵”字,意思是“功德圆满”或“完美无瑕”。就在这声“唵”传入席特哈尔塔耳中的一刹那,他那沉睡的心灵突然苏醒了,他看清了自己行为的愚蠢。
席特哈尔塔深感震惊。他现实的境况就是这样,这么无可救药,误入歧途,背离了一切真敌国,以至于他想自寻短见,而这个愿望,这个孩子般的愿望,却在他心中变大起来:不惜毁灭自己的肉体来求得安宁!这最后时刻的全部痛苦、全部醒悟和全部绝望没能实现的东西,却在“唵”闯入他的意识这一瞬间完成了:他在自己的愁苦和迷乱中认识了自己。
“唵!”他喃喃自语着,“唵!”他想起婆罗门,想起生活的坚不可摧,想起了他已经淡忘的所有神圣的东西。
但这仅只是一刹那,像一道闪电。席特哈尔塔倒在了那棵椰子树下,把头枕在树根上,陷入了沉沉的梦乡。
他睡得很香,没有做梦,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酣睡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他醒来了,觉得仿佛已过去了十年。他听见河水的潺潺流淌声,不明白自己身在何处,是谁把他弄到了这儿。他睁开眼睛,看见头顶的树林和天空十分尺度,回想自己是在哪儿,自己是怎么来的。他想了好长一会儿,往事就像被一层薄纱遮着,显得很远很远,无比遥远,完全无关紧要。他只知道自己已抛弃了过去的生活(在他回忆的最初一瞬间,他觉得过去的生活就像是一个遥远过去的化身,就像是他现在这个自我的一个早产儿)——他满怀厌恶与愁闷,甚至想抛弃自己的生命,但是在一条河边,在一棵椰子树下,他口中念育着神圣的“唵”字,回归了自我,然后便沉沉睡去,而现在又醒来了,作为一个新人观看这世界。他低声念诵着曾使他沉沉睡去的“唵”字,觉得他的沉睡只是一声悠长而专注的“唵”的念诵,一次“唵”的思索,是沉入和彻底到达“唵”之中,到达无可名状的完美境界。
这是一次多么惬意的酣睡啊!从来没有哪次睡眠能使他这么精神焕发,这么神采奕奕,这么年轻活泼!也许他真的已经死掉了,已经消亡,而现在又重新托生为一个新年的躯体?不,他认得自己,认得自己的手和脚,认得他躺在这个地方,认得他胸中的这个自我,这个席特哈尔塔,这个执拗的家伙,这个怪人。不过,这个席特哈尔塔也确实变了,精神抖擞了,令人奇怪地睡足了,显得格外清醒、愉快和好奇。
席特哈尔塔直起身,忽然看见对面坐着一个人,一个陌生人,一个穿黄僧衣、剃光头的和尚,摆出打坐静修的姿势。他细细打量这个既无头发也无胡子的人,看了一会儿,忽然认出这个和尚就是戈文达,他年轻时的好友,那个扳依了活佛的戈文达。戈文达老了,跟他一样,但脸上的神色依然如故,显露出热情、忠诚、探求和忧心忡忡。戈文达这时也觉察到了他的目光,睁开眼看他,但席特哈尔塔发现他并没有认出自己。戈文达见他已醒过来很高兴。显然戈文达已在这儿坐了很久,等着他醒来,尽管并没有认出他。
“我刚才睡着了。”席特哈尔塔说,“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你睡着了。”戈文达答道,“在这样的地方睡觉可不好,这里常有蛇,是森林中野兽出没之处。哦,先生,我是戈塔马活佛的一名弟子,释迦牟尼的信徒,跟一伙同伴走这条路去朝圣,看见你躺在这儿,睡在一个不宜睡觉的危险地方。因此我试图叫醒你,先生,见你睡得很熟,我便单独留下来守护你。显然是我自己也睡着了,而我本来是想守护你的。我失职了,疲劳控制了我。现在你已经醒了,让我走吧,去追赶我的弟兄们吧。”
“谢谢你,沙门,谢谢你守护我睡觉。”席特哈尔塔说,“你们这些活佛的弟子真好。你可以走啦。”
“我走了,先生,祝你永远健康。”
“谢谢你,沙门。”
戈文达行了个礼,说道:“再会!”
“再会,戈文达。”席特哈尔塔说。
和尚愣住了。
“请问,先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席特哈尔塔微微一笑。
“我认得你,戈文达。从你父亲的小屋,从那所婆罗门学校,从参加祭祀仪式,从咱们一起去找沙门,从你在耶塔瓦纳林苑皈依了活佛时,我就认得你!”
“你是席特哈尔塔!”戈文达大声叫道,“现在我认出你了,我不明白怎么竟没能马上认出你!欢迎你,席特哈尔塔,与你重逢我十分高兴。”
“我也很高兴再见到你。你刚才守护我睡觉,我要再一次感谢你,尽管我并不需要人守护。你去哪儿,朋友?”
“我不去哪儿。我们和尚总是云游四方,只要不是雨季,我们总是从一处赶到另一处,按照规矩生活,讲经,化缘,又动身上路。总是如此。而你呢,席特哈尔塔,你要去何处?”
席特哈尔塔说:“我的情况跟你一样,朋友。我不去哪儿。我仅仅是在路上。我去朝圣。”
戈文达说:“你说去朝圣,我相信你。可是请原谅,席特哈尔塔,你的样子可不像个朝圣者哇。你身穿富人的衣服,脚穿贵人的鞋子,头发飘散出香水味儿。这可不是一个朝圣者的头发,也不是一个沙门的头发呀!”
“不错,亲爱的,你观察得真仔细,你的锐利眼睛看出了一切。可我并没跟你说我是个沙门呀,我只是说去朝圣。事实上我正是去朝圣。”
“你去朝圣,”戈文达说,“但是,很少有人穿着这样的衣服、鞋子,留着这样的头发去朝圣。我已经朝圣多年,从来没见过一个这样的朝圣者。”
“我相信你说的话,戈文达。可是现在,今天,你偏偏遇上了这么个朝圣者,穿这样的鞋子,穿这样的衣服。请记住,亲爱的:万物的世界是短暂的,多变的,而最为短暂多变的是我们的衣服,我们的发式,以及我们的头发和身体。我身穿一个富人的衣服,这你没看错。我这样穿戴是因为我曾经是个富人,而我的头发像花花公子,也因为我曾经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现在呢,席特哈尔塔,现在你是什么人?”
“我不清楚,我知道得跟你一样少。我正在半路上。我曾经是富人,但现在不是了,而明天我将是什么,我自己了不清楚。”
“你失去了你的财产?”
“我失去了财产,或者说是它失去了我。反正是没了。造化之轮飞转,戈文达。婆罗门席特哈尔塔如今安在?沙门席特哈尔塔如今安在?富商席特哈尔塔如今安在?短暂的东西在迅速地变换,戈文达,这你明白。”
戈文达久久的凝视着自己青年时代的好友,眼睛里含着疑虑。随后,他像问候贵人那样向他致意,就动身上路了。
席特哈尔塔面带微笑地目送他远去。他仍然热爱戈文达,这个老实而忧心忡忡的人。在这个时刻,在酣睡之后这个美好的时刻,他周身已被“唵”渗透,怎么会不爱别的人和别的事呢!通过睡眠和“唵”而在他身上发生的魔力就在于此:他热爱一切,对见到的一切都洋溢着欢乐的爱。现在他觉得,先前他之所以病和那么重,就是由于他什么都不爱,谁都不爱。
席特哈尔塔面带微笑地目送远去的和尚。酣睡使得他精神焕发,但是饥饿也在折磨他,因为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而他能够顽强地抗住饥饿的时候早已过去了。他既忧伤又欢欣地回想起那个时候。他记得自己当年曾在卡玛拉面前夸耀过三件事,说他会三样高超的不可战胜的本领,即斋戒——等待——思考。这是他的看家宝,是他的威力所在,是他的结实的棍子,在青年时代勤奋而艰苦的岁月里,他就是学会了这三样本领,岂有他哉!如今他已丢弃了它们,它们已荡然无存,他不再斋戒,不再等待,不再思考,他用它们去换取可鄙之物,换取一时的快乐,换取感官的享受,换取奢侈的生活,换取了财富!实际上他的境况很古怪。现在看来,他真的成了孩子般的俗人。
席特哈尔塔思考着自己的处境。他觉得思考已相当困难,他根本没兴趣,可是仍强迫自己思考。
他想,现在我又摆脱了一切如过眼烟云之事,我又站在了阳光下,就像当初我还是个小孩子时那样。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学过。真怪呀!现在我已不再年轻,我的头发已经花白,我的体力已经衰退,却又要从头开始,从小孩子时开始!他忍不住笑了。是的,他的命运真怪!他每况愈下,现在又空空地、赤裸裸地、愚蠢地站在这世界上了。不过,他并不忧虑,不,他甚至感到很想大笑,笑自己,笑这个古怪荒唐的世界。
“你在往下走啦!”他喃喃自语道,边说边笑,边说边把目光投向河面,看见河水也在往下流,不断地往下流,吟唱着欢快地往下流。他很高兴,朝河水亲切地微笑。这不就是曾经想溺死自己的那条河么?那是在一百年前,还是他在梦中见过?
我的生活确实古怪,他想,走过了奇怪的弯路。少年时,我只知道敬神和祭祀。青年时,我只知道苦行、思考和潜修,探索婆罗门,崇拜阿特曼之中的永恒。作为青年人,我仿效那些忏悔者,生活在森林里,忍受酷暑与严寒,学会挨饿,教自己的身体麻木。接着,那位活佛的教诲又奇妙地启迪了我,我感到关于世界统一性的认识又在我体内犹如自身的血液一样循环不已。可是,后来我又不得不离开了活佛以及他那伟大的真知。我走了,去向卡玛拉学习爱之欢乐,跟卡马斯瓦密学做买卖,积攒金钱,挥霍金钱,学着娇惯自己的肠胃,学着迎合自己的感官。我就是这样混了好多年,丧失了精神,又荒疏了思考,忘掉了统一性。就好像我慢慢绕了个大弯,从一个男子汉又变成了孩子,从一个思索者又变成了孩子般的俗人,不正是这样么?这条路也曾经美好过,我胸中的鸟儿并没有死去。然而,这又是怎样的一条路哇!我经历了那么多的蠢事,那么多的罪恶,那么多的错误,那么多的恶心、失望和苦恼,只是为了重新成为一个孩子,以便从新开始。但这显然是正确的,我的心赞成,我的眼睛为此而欢笑。我经历了绝望,甚至堕入了最最愚蠢的想法,也就是自杀的想法,以便能得到宽大,重新听到“唵”,重新睡得好并且适时地醒来。为了能在我心中重新找到阿特曼,我不得不成为一个傻瓜。为了能重新生活,我不得不犯下罪孽。我的路还会把我引向何处?这条路怪里怪气,它绕着8字形,也许是在兜圈子。随它怎么走吧,我愿意顺着它走下去。
他奇异地感到自己的胸中快乐在翻腾。
他扪心自问:你这种快乐从何而来?也许它来自这次使我十分惬意的长长的酣睡?或是来自我念出的那个“唵”字?或是来自我的逃遁,我终于逃脱了,重新自由了,像一个孩子站在了蓝天下?哦,这样摆脱了羁绊、这样自由自在是多么美好!这儿的空气是多么纯净、美好,呼吸起来是多么畅快!而在我逃离的那个地方,一切都散发出油膏、香料、美酒、奢侈和懒散的气味。我是多么憎恶那个有钱人、饕餮者和赌徒的世界啊!我是多么憎恨我自己,恨自己在那个可恶的世界里待了这么久啊!我是多么憎恨自己,掠夺自己,毒害自己,折磨自己,使得自己又老又坏啊!不,我永远也不会再像那样自以为席特哈尔塔聪明过人了!但这次我确实干得漂亮,我很满意,我要赞美,我终于结束了对自己的憎恨,结束了荒唐、无聊的生活!我赞美你,席特哈尔塔,在经过了多年的愚昧之后,你终于又有了一个想法,做了一点事,听见了胸中那只鸟儿的啼鸣,并且随它而去!
他就这样赞美着自己,对自己很满意,并且好奇地听着肚子里咕咕直叫。他觉得,在最近的时日里,他已尝够了痛苦与烦恼,一直至绝望得要死。这样也好。不然他还会在卡马斯瓦密那儿待很久,赚钱,挥霍钱,填饱肚子,却让心灵焦渴难忍。不然他还会在那个温柔的、软绵绵的地狱里住很久,那也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了:那个彻底失望和绝望的时刻,他悬在滚滚流淌的河面上,准备自尽的那个极端的时刻。他感受到了这种绝望,这种极深的厌恶,但是他没有被压倒。那只鸟儿,那快乐的源泉和声音,依然活跃在他心里。他为此而深感快乐,为此而欢笑,花白头发下的脸为此而容光焕发。
“这很好,”他想,“把应当知道的一切都亲自尝尝。世俗的欢娱和财富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我从小就学过。我早就知道,可是现在才算是亲身体会到。现在我明白了,不仅是脑子记住了,而且是亲眼目睹,心知肚明。好极了,我总算明白了!”
他久久地思索着自己的转变,细听鸟儿欢快的鸣啭。这只鸟儿不是已在他心中死去,他不是感觉到鸟儿已经死了吗?不,是别的什么在他心中死去了,是某种早就渴望死去的东西。那不就是他以前在狂热的忏悔年代里想扼杀的东西吗?那不就是他的自我,他的渺小、不安而又自负的自我,他曾与之搏斗了多年却总是失败的自我,在每次抑制之后又再次出现、弃绝欢乐和带来恐惧的自我吗?那不就是今天终于在这河边树林里死去的东西吗?不正是由于这一死亡,他现在才像个孩子,满怀信心,无所畏惧,充满了欢乐吗?
席特哈尔塔还明白了,当年他作为婆罗门,作为忏悔者,在与自我的斗争中为什么会白费力气。是太多的知识阻碍了他,太多的圣诗,太多的祭祀规矩,太多的苦修,太多的行动与追求!他原来十分高傲,自以为总是最聪明,总是最热诚,总是比所有人先行一步,总是博学和多思,永远是僧侣或智者。他的自我就潜藏在这种僧侣气质、这种高傲和这种睿智里,在那儿扎根、生长,他还以为能用斋戒和忏悔来抑制呢。现在他明白了,明白好秘密的声音是对的,没有任何老师能解救他。因此,他只好进入世俗世界,迷失在情欲和权力、女人和金钱之中,成为一个商人、赌徒、酒鬼和财迷,直到僧侣和沙门在他心中死去。因此,他只好继续忍受丑恶的岁月,忍受恶心,忍受空虚,忍受一种无聊的不可救药的生活的荒唐无稽,直到结束,直到苦涩的绝望,直到荒浮选之徒席特哈尔塔、贪婪之徒席特哈尔塔能够死去。他死去了,一个新的席特哈尔塔已从酣睡中醒来。他会衰老,将来有一天他也会死去,席特哈尔塔不是永恒的,任何生命都是短暂的。但今天他年轻,是个孩子,这个新的席特哈尔塔充满了欢乐。
他思索着这些想法,含笑倾听着肚子里的声响,心怀感激地听到了一只蜜蜂的嗡嗡声。他愉快地望着滚滚流淌的河水,从没有哪条河像这样使他欢迎,他从没听过流水的声音是这么有力和悦耳。他觉得河水似乎想对他诉说什么特别的东西,诉说什么他还不知道、有待他领会的东西。席特哈尔塔曾想在这条河里自溺,原来那个疲乏和绝望的席特哈尔塔今天已在这里淹死了。而新的席特哈尔塔对这奔涌的河水感到一种深深的爱,心里暗自决定,不再很快地离开它。
船夫
席特哈尔塔心想,我要留在这河边,当年我在投奔那些孩子般的俗人路上渡过的就是这条河,一位亲切友好的船夫渡我过了河,现在我要去找他。离开他的茅屋之后我曾步入了一种新生活,而现在那生活已经陈旧衰亡了——但愿我现时的路、现时的新年生活能从那儿开始!
他深情地注视着奔腾的河水,注视着这一片清澈的碧绿,注视着这幅充满神秘的画面的透明线条。他看见从水底深处冒起明亮的珠串,平静的气泡飘浮在光洁如镜的水面上,湛蓝的天空倒映在水中。河水正用千万双眼睛盯着他,有绿色的、白色的、透明的,还有天蓝色的。他多么爱这条河呀!河水使得他心旷神怡,他多么感激它呀!他听见心里有个声音在说话,一个新觉醒的声音对他说:爱这条河吧!留在它这儿吧!向它学习吧!噢,是的,他愿意向它学,他愿意倾听它的声音。谁若是了解这条河及其秘密,他觉得,也就会懂得其他许多东西,许多秘密,所有秘密。
但今天,他只看到了这条河的许多秘密之中一个最扣人心弦的秘密。他看到:河水流啊流,永不停息,却又总是在这里,永远是原样,但它又每时每记得都是新的!哦,有谁能了解这点、懂得这点呢!他不懂得不了解这一点,只是感觉到激起了联想,遥远的回忆,美妙的声音。
席特哈尔塔站起身,饥饿已使他无法忍受。他动情地沿着岸边的小路漫步走去,迎着河水,倾听着流水声,倾听着腹内的饥肠辘辘声。
他来到渡口,小船正泊在原处,依然是当年那个渡过他过河的船夫站在船里。席特哈尔塔认出了他,他也显老了很多。
“你愿意渡我过河么?”他问。
船夫见一以一个如此高贵的人竟独自步行前来,很惊奇,把他接上船撑离了岸边。
“你选择了一种美好的生活。”客人说,“每天在这河边生活,在这河面上行船,一定十分美好。”
船夫微笑地晃动着身子说:“是很美,先生,正像你说的那样。可是,每一种生活,每一种工作,不都是很美好吗?”
“也许是吧,但我还是很羡慕你这个行当。”
“啊,你很快就会没兴趣的。这可不是衣着华丽的人干的活儿。”
席特哈尔塔笑了:“我今天已经因为这身衣服惹人注意过,让人猜疑过了。船夫呀,你是否愿意要我这身惹麻烦的衣服?因为你要知道,我没钱付你摆渡费呢。”
“先生是在开玩笑吧。”船夫笑道。
“我没有开玩笑,朋友。你瞧,你曾用你的船送我渡了一次河,没收钱。今天也还是照样吧,请收下我的衣服。”
“先生莫非要不穿衣服继续赶路?”
“啊,我现在最希望的是根本不用再赶路。船夫呀,最好你能给我一件旧围裙,收我做你的助手,更确切地说是做你的徒弟,因为我得先学会撑船才行。”
船夫久久地探询地注视着这个陌生人。
“现在我认出你来了。”他终于说道,“你在我的茅屋里睡过觉,那已经很久了,大概有二十多年了吧。当年我把你渡过河,然后咱们就像好朋友一样分手了。那时你不是沙门吗?你的名字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我叫席特哈尔塔。上次你见到我时我确实是个沙门。”
“那么我欢迎你,席特哈尔塔。我叫瓦苏代瓦。我希望你今天还是做我的客人,睡在我的茅屋里,给我讲讲你从哪儿来,你的华丽衣服为什么成了你的累赘。”
他们已来到河中心,瓦苏代瓦加紧划桨,逆水前进。他用有力的胳臂平静地工作着,目光盯着船头。席特哈尔塔坐着看他,忆起当年他做沙门的最后一天,他心中就曾对此人产生过热爱。他感激地接受了瓦苏代瓦的邀请。靠岸后,他帮船夫把小船在木桩上系好。然后,船夫请他走进茅屋,给他端来面包和水,席特哈尔塔吃得津津有味,而且还吃了瓦苏代瓦款待他的水果。
后来,日落时分,他们俩坐在岸边一棵树的树干上,席特哈尔塔给船夫讲自己的出身和生活,那些绝望时刻的情景就像今天一样历历在目。他一直讲到夜深。
瓦苏代瓦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仔细地倾听一切,出身和童年,所有的学习,所有的探索,所有的欢乐,所有的痛苦。善于倾听正是瓦苏代瓦的重要美德之一,能像他这样倾听的人不多。他并没有说一句话,讲述者就感觉到他把话全都听进去了。他安静、坦诚和期待地听着,一字不漏,没有丝毫的不耐烦,也不作褒贬,只是倾听。席特哈尔塔感到,能向这样一位倾听者诉说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探索和自己的烦恼,实在是一件幸事。
当席特哈尔塔快讲到结尾时,他讲到河边那棵树,讲到自己的潦倒落魄,讲到那神圣的“唵”,以及他如何在睡了一觉之后对河水深感热爱。这时,船夫听得更是加倍专心了,他全神贯注地闭着眼睛听。
等到席特哈尔塔说完了,而且出现了很长时间的沉寂之后,瓦苏代瓦才说:“情况正如我所想,河水跟你说了话。它也是你的朋友,跟你说了话。这很好,好极了。你就留在我这儿吧,席特哈尔塔,我的朋友。以前我有过妻子,她的床铺就在我的旁边,可是她早就过世了,我已经单身生活了很久。你跟我一起过吧,住处和饭食都够两个人的。”
“我感谢你,”席特哈尔塔说,“谢谢你,我同意。瓦苏代瓦,我还要感谢你这么专心地听我讲!善于倾听的人极少,我从没遇见过像你这样善于倾听的人。在这方面我也要向你学。”
“你会学到的,”瓦苏代瓦说,“但不是跟我学。是河水教会了我倾听,你也该跟它学。它什么都懂,这条河,可以向它学习一切。瞧,你已经向它学到了一点,那就是努力向下,沉下去,向深处探索,这很好。富有而高贵的席特哈尔塔变成划船的伙计,博学的婆罗门席特哈尔塔变成船夫,这也是河水点拨你的。你还会向它学到别的东西。”
又经过了一个长长的间歇,席特哈尔塔才说:“还有别的吗,瓦苏代瓦?”
瓦苏代瓦站起来。“夜深了,”他说,“咱们睡吧。我不能告诉你‘别的’是什么,朋友。你会学到的,兴许你已经知道了。瞧,我不是学者,我不擅长讲话,也不擅长思索。我只善于倾听,心地善良,别的特长就没有了。要是我能说会道,说不定会是个贤人呢,可我只是个船夫,我的任务就是送人们过这条河。我摆渡过许多人,成千上万人,他们都认为我这条河只是他们旅途上的一个障碍。他们出门旅行是为了挣钱和做买卖,去参加婚礼,去朝圣,而这条河正好挡在他们路上,船夫就是要帮他们迅速越赤这个障碍。但是,在这成千上万的人中间有几个人,为数很少的几个人,四个或者五个,这条河对于他们不再是障碍,他们听见了河水的声音。他们凝神细雨听,这条河对于他们变得很神圣,就像对于我这样。不过,咱们还是休息吧,席特哈尔塔。”
席特哈尔塔留在了船夫身边,跟他学习撑船。如果渡口没事可做,他就和瓦苏代瓦下稻田干活,拾柴禾,摘芭蕉。他学习制作船桨,学习修补渡船和编篮子,对所学的一切都兴致勃勃。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而河水教给他的东西比瓦苏代瓦教的更多。他不断地向河水学习,首先是学习倾听,以平静的心境倾听,以期盼和坦诚的心灵倾听,没有激情,没有热望,没有判断,也没有见解。
他在瓦苏代瓦身边愉快地生活。两人偶尔交谈,只说数量不多的深思熟虑过的话。瓦苏代瓦并不健谈,席特哈尔塔很少能激起他的谈话兴致。
有一次他问瓦苏代瓦:“你是否向河水学到了这个秘密:时间并不存在?”
瓦苏代瓦脸上露出了爽朗的笑容。
“是的,席特哈尔塔。”他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河水到处都是一样的,在源泉头,在河口,在瀑布,在渡口,在急流,在大海,在山区,到处都一样,对于它只有现在,而没有将来的阴影?”
“是这样。”席特哈尔塔说,“我当弄明白这点后再细看自己的生活,就发现它也是一条河,少年席特哈尔塔和成年席特哈尔塔以及老年席特哈尔塔都只是被影子隔开,而不是被现实隔开。席特哈尔塔先前的出生并不是过去,而他的死亡与回归婆罗门也并非将来。万物无过去,万物过将来;一切都是现在,一切都只有本质和现在。”
席特哈尔塔兴奋地侃侃而谈,这种大彻大悟使得他十分高兴。哦,一切忧患不就是时间吗?一切自我折磨和自我恐惧不就是时间吗?一旦超越了时间,一旦抛开了时间,世上的一切艰难困苦和敌对仇视不就一扫而光了吗?他说得兴致勃勃。瓦苏代瓦只是精神焕发地朝着他微笑,点头赞许。他默默无言地点头,用手抚摩席特哈尔塔的肩膀,然后便转身去做自己的事了。
又一次,正值雨季河水暴涨,水流湍急,席特哈尔塔说:“哦,朋友,河水有许多声音,非常多的声音,对吗?它是不是有一个君主的声音,一个兵士的声音,一头公牛的声音,一只夜鸟的声音,一个产妇的声音,一个叹气者的声音,以及上千种别的声音?”
“是这样的。”瓦苏代瓦点点头,“在河水的声音中包含了所有生物的声音。”
“你知道吗,”席特哈尔塔接着说,“当你同时听到了它的全部上万种声音时,它说的是哪个字?”
瓦苏代瓦脸上绽出了幸福的笑容。他俯身凑近席特哈尔塔在他耳边低声说出了那个“唵”字,而这也正是席特哈尔塔所听到的字。
一次又一次,席特哈尔塔的笑容与船夫的笑容越来越相似,几乎同样神采奕奕,几乎同样幸福得放光,同样从那上千条强国富民的皱纹里闪闪放光,同样的孩子气,也同样的老态龙钟。好多旅客看见这两个船夫都以为是兄弟俩。晚上,他们经常一起坐在河岸边的树干上,默然无语地倾听河水流淌,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水,而是生活的声音,存在的声音,永恒发展的声音。有时,两人在倾听河水时想到同样的事,想到前天的一次谈话,想到他们的一个船客,那人的脸色和遭遇引起他们的北京白癜风医院北京白癜风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