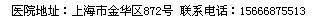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舌系带短缩 > 基本特征 > 苗雨田中篇小说青春色泽连载七
苗雨田中篇小说青春色泽连载七
(七)
旧历年的鞭炮声,从年三十天色黑定以后,开始陆续加剧着爆响,各处蓦然间腾升而起的种种璀璨夺目的壮丽焰火,使得本来就掩映在一片灿烂灯火之海的县城,完全沉浸在了汪洋般辉煌壮阔的丰腴之中。
从来都是在石峁村过年的邦浩轩,显然被眼前的壮美景色所深深地震撼了。他站在瑞新公司的楼顶之上,穿过满耳脆响,掠过满眼辉煌,不由地向着故乡的方向遥遥地张望过去。目及黑漆漆的天际之尽,他的脑海里便清晰地浮现出石峁村此时此刻的年夜景象,黑沉幽邃的夜幕之下,零星摇曳着点点碎银似的灯光;劈啪撒落的鞭炮声应和着偶尔炸响的“二踢脚”,显现出农家大年三十夜晚的安谧祥和、深远古朴、神奥籁韵。
此刻,邦浩轩孤单地站立于楼房之上,既不属于眼前的这壮丽辉煌,又不属于故乡的那神奥古朴;他突然觉得,自己是属于那黑漆漆的天际之尽的了。那里虽然看不出有丁点儿的光亮,但这却合乎他此时的心境。
除夕的前一天,门房的老李也回家与儿孙们团聚去了,偌大的一个瑞新公司,如今就只剩下邦浩轩一人独守空门了。
他切了几片肉,撒几根挂面进去,草草吃了年夜饭后,就将早已挂在楼角的那一长串鞭炮悄悄地点燃,独自一人在炮光中欢呼着辞旧迎新……
突然,炮声一停,他那激奋着的情绪也跟着熄灭了。他立刻觉得整座楼房向他压迫过来,那种黑乎乎的感觉使他更加孤苦难耐。终于,他摸爬着上到了楼顶。
在楼顶上环望遐想了好些时候,他渐渐感到周身的凉意一阵猛似一阵地袭上了心头。这时,他突然条件反射般地想到了俩人。这两个女人在心头猛一闪现,使他孤单凄寒的心境顿然觉得坚强、温暖了许多。
他首先想到了给他以生命的母亲。母亲在失去父亲后,依然在和命运做着最顽强的抗争,以她那年过半百的弱妇之躯,拼死挣活地帮衬扛托起他们兄弟三人的涉世重担。接下来,他自然想到了给他生活以倾力帮助,给他灵魂以无限慰藉的甄梅。甄梅在他高考落榜走投无路之时,帮他找到了这份工作,并一直以独特的情意,鼓励他奋斗成才。前几天,她放寒假刚回到家里,不知从哪里听说到他过年值班没有铺盖、灶具后,竟从自己家里偷偷地搬来了一大堆,供他使用。他当时黑着脸拒绝着她的这番好意,背后却偷偷地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邦浩轩思前想后,思绪麻乱地从楼顶下来,毫无目的地在楼道口踱来踱去。他现在还不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很害怕大年夜里的这份独处。
他完全相信,异常的孤苦与沉寂真是可以将人给吞噬掉的。
“咣当!”随着一声清脆的锐响,邦浩轩的筋骨瞬时被挤缩成团。
“咣!——咣当当!”锐利的响声稍作迟疑后,再次开始震响。邦浩轩毛发直竖,恍惚判断出这异样的响动来自空旷的院落。有关大年夜里的种种恐怖传说骤然袭上心头。他隐约感觉到,暗夜里的种种鬼怪正向这里冲涌奔突而来……他十分后悔自己非但没有在门口窗前安刀立锯放火防范,反倒登高观景如寻常一般地大意着了。他压抑着急促的喘息声,一闪身躲入了房间,然后关死了房门,再不敢贸然外出。
“咣咣!当当!咚咚!……”锐利的撞击声异常急迫地刺破门窗玻璃,直击邦浩轩的心窝而来。他本能地拾起了门背后一根粗实的铁棍,将它紧紧地捏在手里,屏息谛听着外面的动静,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突然,他听到了一个似曾熟悉的声音。
他逐渐辨清了是在呼唤他的名字。
听逝去的父亲曾经讲过,年三十若有人在门外喊你的名字,是万万不可应答的。邦浩轩禁不住抖索着身子,既不答应,也不肯出去。
“邦浩轩!邦浩轩,快开门!——咚!咚咚咚!邦浩轩!我是甄梅!我是甄梅!”
邦浩轩一把抓起桌子上的大门钥匙,将铁棍撂在了一边,满心愉悦地奔出了门外。
甄梅和自家的保姆在给邦浩轩带来了鸡鸭鱼肉山珍海味等等丰盛的年夜饭的同时,还给他孤苦凄怆的灵魂带来了新异清媚的阵阵春风。甄梅眉笼新月,保姆脸拂春桃,邦浩轩的心间顿然装满了蜜。
“今晚果真不回家了?”邦浩轩甩出了红桃K,等着甄梅出牌时,盯住她清水般毛酥酥的双眸说,“父母大人怪罪下来,我可承受不起呀。”
“放你七十二个心吧,”甄梅思索了半天,出手打出了“大王”后,莹浸玉洁的双手轻巧地将牌合拢回去,秀丽含馨的一张脸向着邦浩轩迎来,满不在乎地说,“我呀,早给爸爸、妈妈说了,是去给爷爷、奶奶拜年的,晚上就陪爷爷、奶奶过年,不回去了。哈哈,到爷爷、奶奶那里,俩老人早早地就被我俩安顿着睡下了……这不,我们就过来陪你了?”
“咯咯咯……”俩姑娘银铃般的笑声肆无忌惮地洋溢着盈满了小屋。甜丝丝的笑声漾及邦浩轩的心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刹时泛滥在了他的心际。
此后的时日里,甄梅不时前来,陪同邦浩轩一起值班,但却再未将保姆一同带来。邦浩轩看出了这一点,就问甄梅说:“你家保姆回老家了?”
“没有呀?!”甄梅略有惊讶地又说,“你问这干啥?”
“没啥,没啥,只是随便问问。”邦浩轩一脸诚恳。
“噢,对了。我家保姆说她也是石峁村人。你不认识她?”
“她认识我?”
“这倒没听她说过。”
“她姓啥?”
“姓杨,叫——对!叫杨彩飞。”
“杨彩飞?杨——”邦浩轩思索着,突然茅塞顿开般地豁然说道,“她父亲叫杨狗吃,她姐姐叫——”邦浩轩本想说,“她姐姐叫杨秀柳。”但话到嘴边又突然停定在了那里,就好像顺利地吸溜到嘴边的一条鱼,在即将吞入到喉咙的一刹那,突觉有鱼刺从中冒出,紧急迫使他中断了吞咽。
这根鱼刺,正是杨秀柳。杨秀柳曾是他哥哥订婚后又散掉的媳妇。邦浩轩当然不会怪怨杨秀柳,更不会罪责杨家的任何一个人,他只是在提起杨秀柳这个名字时,突然暗自悲伤起来,竟不能继续说下去了。
甄梅也察觉到,只要一提起家乡的某些事情,邦浩轩往往就会变作一脸愁苦状,显得特别脆弱而不堪一击,与平常完全判若两人。现在,从他那吞吞吐吐的话语中,她已敏锐地捕捉到了他似有被刺痛的隐情。她本想问清其中的因由,但又怕引起他的伤痛,遂朗然一笑,转移了话题。邦浩轩当即从甄梅那聪明的圆场中,感知到,甄梅正是那杯善解人意的神爽的米醋,倾刻间,已将他入喉的鱼刺软软地化掉了。
春节值班,其实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工作要做。邦浩轩挣着双倍的工资,除了照看好公司的门户外,倒显得有几分清闲悠然。加之有甄梅不是来送吃送喝送书送报,就是于闲暇时约好去逛街跳舞,生活过得充实而甜蜜。邦浩轩本不会跳舞,但是在甄梅的指教下,他已经逐渐喜欢上了这项有节奏地推拉摇移、搂近抱贴的甜软运动。
起初,他左手轻握着甄梅绵软的右手,右手却怎么也不好意思搂按着她那柔软颤滑的纤嫩细腰。他就只好用右手食指和中指,使劲地配合着那只大拇指,似天女绣花一般,轻渺地捏捻起她腰际的一些绵软,心际渴求,眼睛却躲闪着甄梅那一双毛酥含情的明眸,浑身颤栗、扭摆着谨小慎微地步入舞池……
摇出几步后,他的那只轻扶于她腰际的胆小的手儿就被她的一只温柔的小手儿轻轻地按伏了下去。他立刻受到鼓舞,那手便大胆地紧紧熨贴在了她的那片柔软的福地。他顿觉有股柔和的春风在心湖泛开后漾及了全身。迷醉的霓虹灯下,他的身子一阵颤栗后,就被甄梅这只娇柔甜绵的毛虫儿紧紧地缠附了过去……
他们双双滑步舞池,相互间都有了一种拥着云团的感觉。
这天,当邦浩轩和甄梅在歌舞厅再次翩然起舞,正愉悦着相互坠入了对方的那团云雾之中时,甄梅的男朋友孙光华突然间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当时,甄梅的那张俏脸伏在邦浩轩的肩头,甜美的小嘴儿正对着邦浩轩的一只耳朵,专注地吹着蜜儿。这时,邦浩轩突见有人神色怪异地走上前来,他稍一愣怔后,辨出了来人正是孙光华。这当口,他猛然间就将正拥裹在怀中的甄梅推到了一定的距离;紧接着,他就打算甩脱开被甄梅缠绕着的手臂,立刻躲闪到一旁的座位上去。但是,邦浩轩躲离的动作毕竟已迟钝了半个节拍,他还是无可避免地和孙光华打了个尴尬的照面。
“光——光华,你——你来了?快陪甄梅跳几圈吧。你们跳吧!”邦浩轩涨红着的脸上堆着笑,边说边急忙隐入了人群,即刻便消没了。
完全处在兴头之上的甄梅,冷不丁被邦浩轩搡在了一边,又惊愕地面对逼近而来的孙光华,她水嫩平静的一张脸,刹时翻搅扭曲得失去了光泽。
“梅!我终于找到你了!”孙光华如获至宝地抓住了甄梅的一双手,惊喜地露出了单纯而灿烂的笑容,异常欢欣地说,“……唉?邦浩轩哪去了?我请大家吃夜市(去夜市吃饭),顺便向你拜个晚年,道个歉!都怪我回农村老家去过年太忙,让你受冷落了”。
“你回老家过年了?”甄梅长长地吁了口气,借风使舵地轻巧着问他。
“对呀!我那天在电话中不是给你说过了吗?”孙光华笑着,声音有点大。
甄梅用心回忆了半天,确信有过这事,便不好意思地向他点头微笑。
孙光华轻轻拉起甄梅的一只手。甄梅顺从地跟随着他,离开舞池,步入了夜市。在夜市一雅间入座后,孙光华说,再去找找邦浩轩,让他一同来吃饭吧。甄梅轻轻地摆了摆手,孙光华就收回了迈出门栏的一条腿,复又安坐了下来。待四目相对后,孙光华顿觉有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意飘摇着浮上了心头。
此后,甄梅再去邦浩轩房中时,便带来了保姆杨彩飞,有时还会有孙光华一同前来。
四个年轻人走在一起,总是充满了无以穷尽的欢乐,当然也有几分缠绵纠结着的隐情包含其间。这四个人里,除保姆而外的三人之中,轴心无疑是甄梅。但是,就眼下而言,甄梅却并未确定自己轴心的滚动范围。甄梅明着与孙光华相恋,暗中却又依恋着邦浩轩;她明着协助着邦浩轩,暗地却有背离孙光华的倾向。当然,甄梅心里也明白,若单从感情角度来考虑,她爱慕的人无疑是邦浩轩。邦浩轩长得高大俊俏,飒爽英姿,和她谈得来、说得上,是她少女初恋的人儿;孙光华则个矮脸削,琐碎缠绕,一派小市民气息,若不是他老盯着她不放,处处对她殷勤周到,逆顺和合,她早就和他分手了。但是,若是从现实的角度考虑,甄梅还是觉得不能和孙光华轻易说出“byebye”的话来。怪只怪,邦浩轩不争气,未能考取大学,尽管她想方设法为邦浩轩谋出路,但她毕竟还是一个身在校园里的弱女子呀,她除了倚仗自己良好的家庭背景为他找到这份临时工外,她还能为他做什么呢?有时候,她头脑发热,真想不再去考虑那么多,就和自己心爱的邦浩轩私定终身算了。但冷静一想,前有父母、家庭的阻力,后又有孙光华的压力,思前想后,她还是考虑,等到大学毕业了,真正到了该嫁人的年龄再做决定吧。因此,她现在的这根轴心就异常矛盾地一会儿滚在了孙光华的这边,一会儿又偏向了邦浩轩的那边。这正如她日记中写道:谁说少女无忧愁,情郁家恨泪纷柔。
春节值班过后,邦浩轩付清了先前的房租,复又搬回到了原来租住着的那间小屋。住回到阴暗冷潮的房子之后,他突然显得孤苦难耐,浮躁不安。这种痛苦的感觉令他莫名地忧伤、悲凉,无以自拔。他一会儿感觉自己是个找不着家的孩子,正忧心焦躁地在独自跋涉;一会儿又感觉自己是掉队的孤雁,正声声哀鸣着在长空飞掠;有时,他又感觉自己是临将就木的老人,满心里在一遍遍地回忆着往昔的旧事,在所有这些往事中,却总是难以脱离开一个鲜活的人影。
这人儿当然就是甄梅。
他现在实在难以说得清楚,自己对甄梅是感激、羡慕还是充满着爱意。若说是感激,他觉得分量太轻;若说是爱慕,他又觉得高不可攀。他悲叹自己资质浅乏,更提醒自己不能与甄梅有太多太密的接触,若那样,非但报答不了甄梅对自己的一片好意,反而会连累毁掉她光明前程的呀!
那么,他为何又要在心里一遍遍地呼唤着甄梅的名字?为何又要对甄梅充满难以遏止的渴求?邦浩轩深处这一矛盾的夹缝,百思不得其解,百般努力却难以求得片刻的轻松与宁静。
后来,因为一个人的出现,使他终于从这一矛盾的焦虑中逐渐安定了下来。
使邦浩轩最终从那因依恋而悲伤、因无望而痛苦、因躁动而耗神的情感纠葛中得以解脱的不是别人,而正是甄梅家的保姆——杨彩飞。
甄梅的父亲甄珠宝是焦县副县长,她母亲尤荣是县人大副主任,两位县级领导,总有忙不完的会议、汇报,应付不完的监督、检查,家里尽管只有甄梅这一个孩子,却也难以经常照料。大多时候,甄梅总是和奶奶、爷爷及保姆在一起生活。如今,甄梅去省城上学后,家里依然要由保姆来收拾、照料。杨彩飞究竟是甄梅家里雇用的第十几个或第几十个保姆,谁也难以计算得清了,反正,这甄家门上的保姆就如同走马灯似的,总是走了一个又来一个。大多时候,总是青春年少的保姆们难以熬耐得住那奢华的寂寞与软禁般的孤独,兴冲冲地来后,又兴冲冲地走了。
杨彩飞是经由在哇啦镇当老板的她的姐夫的介绍,于春节前一个月来到甄梅家作保姆的。由荒芜贫乏的石峁村,一下子来到辉煌富丽、景鲜色艳的城市;由农村土木结构、塌墙烂院的百姓之家,一下子来到城里这拥有宽敞豪华、精装丽饰的三层小洋楼之居的上好人家,说实话,杨彩飞除了惊诧,就是惊慕;除了大开眼界,就是大长见识。
起初,杨彩飞对这豪华的住宅几乎无所适从,就如同当年《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入了贾府的大观园。特别是她那在石峁村里爬坡上洼涉水淌沙的一双健壮的脚板,如今,却难以在这明光可鉴的地板上自由走动了。有几次,她竟滑倒在地。滑倒后,她还愣呆呆的,不知是怎么回事。她用手在地板上搓过,才发现,这地面竟和她们石峁村的那条冰河一样的光滑。自此,只要感觉脚下稍有溜滑,她便顺势做出溜冰的样式,轻巧极了。尤荣见她如此,忙将一双棉拖鞋拿给她穿。当即,她便感觉行走自如,似从难以站稳脚跟的石峁村的冰河,一下子跋上了可以随意穿行的河岸。
和大多数保姆相类似,这种新奇劲儿一过,杨彩飞就觉得一切也就那么回事儿,只不过就“宛如平常一首歌”而已。
物质第一的退后,直接导致的便是精神第一的上升。杨彩飞身居豪宅,整日吃美味,待贵人,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石峁村,思念着父母亲人。她已经和主人请假回过几次家了,但她还想回无数次、无次数的家。她像一只被豢养入笼的鸟,回家成了她放飞的美梦。
但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现,她的这一梦想就有了改变。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正是同村的老乡邦浩轩。
引起杨彩飞少女心湖波动荡漾的根源来自甄梅。
甄梅后来怎么也想不明白,她当初究竟是做了些啥,做了些啥呀!
其实,这事说来也很简单。大年三十那天,甄梅哄着家人带了保姆杨彩飞出来,伙同邦浩轩共度除夕之夜。三个年轻人玩牌打诨,甚是开心,都感觉是有生以来过得最愉悦爽快的一个大年夜。按说,这事就此便罢,但是回去之后,躺在绵软床铺之中的杨彩飞却心痒脸热,不知从何处躁动而起的情愫久久难以平复。她一遍遍地回忆着打牌时的情景,一点一滴地从脑海里清晰地折射出邦浩轩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举止言谈、笑貌音容……
情窦初开的少女柔情,如春日里飞扬的柳絮,夏日里盛开的花菲,秋日里高浮的白云,冬日里飘舞的雪花,有的是诗情画意,有的是美好想象。
杨彩飞是那种适应性与悟性极高的新时代女孩儿,尽管她今年只有二十一岁,也仅是初中毕业,但她的视野已远远超出了她的学识与年龄。这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她酷爱外出闯荡;二是她爱看电视、喜读书报。而她的这两项喜好邦浩轩刚好也同样具备。她甚至从那短暂相处了一夜之中发现,邦浩轩身上还具有她所无法企及的好多优点,她特别渴望能从他那里得到更多更好的视听,特别渴盼与这位老乡再次相见。但是,不知为什么,当甄梅再次外出时,却并未带她一块儿出去;甚至在她当面向甄梅提出希望和她一块去,去和老乡邦浩轩打探老家、父母等情况时,甄梅还是轻轻地摇摇头。
后来,正当她鼓足勇气,打算独自前往时,甄梅却带着她,终于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地见到了邦浩轩。
对于这位老乡,她见得越多,却越想多见。她实在难以说清,自己为何对他会有如此强烈的奢想与思念?后来,当她看到一部叫《风轻月渺》的电视剧时,她才十分明晰地感觉到自己就是那剧中的女主人公沙丽雅;于是,她就偷偷地将邦浩轩想做了这剧中的男主人公欧罗季,默默地去独品那剧中的情言,心中的蜜意,梦中的思念……
至于她姐姐杨秀柳,曾是邦浩轩的哥哥订婚又散掉的媳妇,双方家庭曾因此而有过很不愉快的过节一事,仔细想来,也正像这部剧中曲折误会的动人情节一般,实属生活中的正常本质,丝毫不会阻挡她对邦浩轩的那份深深的爱意。
《风轻月渺》在耳濡目染中对杨彩飞的影响与感化、启迪与刺激,无疑是深刻而久远的。犹如纯白净洁的一张纸,你一直搁置着不去碰它,它就一直固守保持着那份圣洁;而你一旦要用它来作画书字,那种醒目、定型的程度肯定是会成就、主宰了一切的。杨彩飞纯情清明的一张心灵白纸,显然在这成熟的青春岁月里,被一种无形的萌动、偶然的契合力量轻轻催动着,伺机开始了舒展、飞扬、飘荡,最后终将落在某一方画桌前,开始了着彩。
杨彩飞这颗正处青春萌动的种子,看似娇小柔嫩、幼弱稚黄,其实在人们尚未觉察中,却已经具备了顶崖破石,冒然出土的胆识与魄力。这不,甄梅上学走后还没几天,她就独自急迫地寻找到了邦浩轩的门上。
邦浩轩正在办公室里为甄总起草一份中标合同书,忽听有人在敲门。他只轻轻地“呃”了一声后,仍旧继续伏案忙碌着。这份材料甄总要求在下班前交付、打印,他现在必须要在一小时之内收尾。
“咚咚咚!”敲门声再次急促地响起,像是在有意和他做对。
“啪!”邦浩轩气乎乎地走上前去,很不情愿地将门打开。打开门后,他并未向门外看上一眼,而是急忙复又坐回到桌前,将匆忙中的那份紧急毫无间断地继续下去。
过了大约有一刻钟的时辰,他终于完成了这一关键的核心段落。他稍微直腰抬头,一边回头在那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里仔细推敲斟酌,一边习惯性地伸手去拿放在另一边的茶杯。
突然,他的手心在捏到了一种柔热的同时,还捏到了一种怪异的绵软……
他的目光依然盯着那白纸黑字,思维仍然专注,感知显然迟钝。他不住地搓捻着那种绵软,揉捏着那种温热,终于抬手要将这绵热送入口中。起先他似曾感觉到了一种异样的轻巧。他将它送到嘴边,双唇微启,轻轻地吸了一小口,紧接着他便很不满意地大口吮吸了起来……
刹那间,一种突异的柔热温香,将他彻底震醒!
令他做梦都难以相信的是,这吸入他口中的普通茶水,怎么竟魔幻般地变成了一只纤嫩的玉手呀!
他当即便万分羞愧地惊愕在了那里,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不知自己是谁了。
他听到杨彩飞在低低地啜泣。
他抬眼看她。她的毛毛眼里荡漾着的不是痛苦而是幸福。他即刻感觉到,她的眼灼热而急迫地吸附着他的光芒,似要将他完全融入某种境地。他一阵眩晕,等待着,等待着从未应验过的已知,等待着从未体验过的未知……
突然,杨彩飞扑入了他的怀抱。
他触着了她颤栗的身子,同样惊惶地一阵抖索,阵阵震颤;当杨彩飞扬起红晕美好的一张脸,坚定而焦渴地吻向他的嘴唇、鼻梁、双眼、双颊最后又贪婪地吮吸舌添着他的口唇、他的细牙、他的舌尖舌体的时候,他迟疑措乱的手臂,突然丧失了羞怯顾忌;终于,他无以遏止地紧紧地箍抱住了那所有的温软柔热,紧紧地拥匝住了那所有的美好梦幻……
就在他所有的绵软开始硬朗,所有的骨头开始消融的一刹那,温甜的彩飞却轻轻地挣脱着他,拖移摇挪开了她那紧紧地熨贴着他的柔热的身躯,向着他幸福地梦幻般地笑来。
她轻轻一笑过后,盈满眼眶的泪水继而溢流脸颊,迅即便冲刷淹漫到了那片薄嫩红润的柔唇之中。邦浩轩心中一震,顿觉自己也已融入了那片红润的湿地,并正在被那温热的泪水轻柔细滑地冲刷着,躯体与灵魂一起在那酥软温静的细浪里舒坦愉悦地沐浴着,震颤不止。
他内心突然感觉到,彩飞是温热而贴近的。甄梅却是迷茫而遥渺的了。与此同时,一种深深的矛盾和不安,却即刻盘聚心头。
(未完待续)
苗雨田,神木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