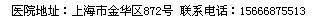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舌系带短缩 > 相关知识 > 长话vol1也许我们会被编成诗歌或
长话vol1也许我们会被编成诗歌或
巷子里的戏院
今年春天,赵北回国,我们两个约在成都见面。夜里11点下飞机,到酒店刚好12点。隔壁几乎一整夜都传来床头嘎吱作响,还有间或的女人叫声,隔着一道墙听起来凄厉惨烈。在宾馆里声嘶力竭叫床的女人像C语言一样,你给她输入一个指令,她给你输出一个相应,有时输入太多太快,她就编译进了一个死循环,CPU放空,两手抓紧床单浑身颤抖,死机了一样百呼不应。
我睡了一个半小时,六点钟起床的时候,纱窗外的双流县绿意葱茏,我想到满是山风的隘口冥想,温泉一样的和风扑着我的脸被我的胡茬梳理,阳光像潮水攀上脚面,又落回谷底。
洗完澡光阵身子躺在床上,我想有一个姑娘,云雨半晌。想到这我的被子中间鼓起了一个包。
我花了九十块钱打车到春熙路,往西走的时候意料之外戏剧性地正碰上赵北从龙抄手一路走过来。
青羊宫的香炉前落了一地去年冬天的竹叶,老道姑擎着香点上,一边抹着香炉边的香灰一边和我们聊天。
可是我俩都听不懂四川话。
四川话是凉糕味儿的。涮红油火锅一定要就着四川话,就像要蘸香油一样。
我有过一个成都的女朋友,笑起来露出一排小白牙,像豆花。我总想把她和着豆瓣和剁椒一口吞下去。她也像凉糕一样软,靠着我的手臂睡一晚,腰和胸脯上会留下粉红的手印。她高傲又温柔,美丽而哀愁。穿着厚实的藏地衣服,她用木筷从黑釉陶碗里衔起纱面吸溜到口中;她披着肥大的衬衫坐在床边蜷起身子剪趾甲。她的这些模样都让我心动,我把舌头伸向她的嘴角去尝面汤,也把五指伸向她的乳房去寻找信仰。
人一旦在肉欲中贪得无厌,就成了情感中的黎丘丈人。在分手两年之后,我又在成都,和赵北走过晚上的宽窄巷子。戏院门口穿青红绸缎衣服的女人捏着手帕,用尖尖的口气讲着稠稠的语言。她们比起她来,真是差得远了。这样想着,我的脑海里一双手又伸向了那年那时裸着上身背对着我读经的她。
“跟我回大连去吧,我去工作你开书店。”
“那里是很好的。可我偏不喜欢。”她那时说,“我想留在成都。”
她捧起面前的一罐酸奶,吸管“噗”地一声刺穿锡纸盖子捅进玻璃瓶子。我浑身一颤。
外婆过世钱被查出结肠癌,据说结肠癌是种有高遗传几率的癌症,从那以医院查肠镜。
女医生戴着蓝口罩,往我的屁股上涂抹冰凉的杀菌也,把蜿蜒逶迤的肠镜对准我的肛门,“噗”地捅了进去,平地起惊雷,我被冰得浑身一颤。像豢养了一条冰凉冷血的蛇,在我的腹腔里狼奔豕突。
她眯着眼盯着屏幕,手上的动作娴熟自如,我猜在她眼里我和一只被检疫的猪没什么分别。女医生的白色乳胶手套让我想起东莞、毒龙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词汇。
我扭头看一眼女医生,想到这样的羞耻play每两年要再温习一次,直接导致了我时常会梦见一条铁触手趁着我熟睡侵占我的后方。那种梦魇无时不刻不在提醒着我同性恋有多可怕,于是我逆着时代潮流,成为了一个恐同又歧同的人。男人和女人可以面对面爱抚和深入,而两个男人却只能像两只野兽,一前一后、一个弯腰曲腿另一个抱臀挺腹。然而让我坚定恐同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发生在我大四时的一件事。
我和社团的社长到其他学校交流,住在天津一家假日酒店的同一个房间。晚上他洗完澡,光着身子揍出来,摇晃着不堪入目的下半身。在我瞠目结舌的时候他从包里翻出了一管润滑剂,撅着屁股开始抹了起来,就像要做肠镜检查一样。
“你……干嘛?”我想要声色俱厉,却难掩恐惧。
“来干我啊!”他凑了过来。
我眼疾手快,抓起外套和背包,夺门而出。他在后面还在发出令人作呕的呻吟。
我在滨海新区的海边逛了一夜,风吹得我涕泗横流。从那以后,无论是在网络还是影视作品中,每看到提及男同性恋,我都能感觉胃里一阵痉挛,避之不及。我无权评述对错,只是对心里的恐惧阴影望而生畏。
在饭店赵北给我点了一碗燃面,我从酸奶瓶、肠镜以及其他的脑部混乱中挣脱出来。旁边桌一个东北口音的女人对男人说:“我想吃包子嘛。”
“吃什么包子!晚上教你吃飞机!”那男人吼。
赵北噗地笑了,喷了一桌子的粉蒸肥肠。
本文版权属原作者所有,转载拷贝请注明作者姓名及来自逸说yishuo_24北京治疗白癜风专业医院北京哪个医院医治白癜风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