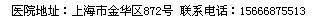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舌系带短缩 > 相关知识 > 连载辉发河传第四章古怪的场院
连载辉发河传第四章古怪的场院
恩存按
小说,一种展示作家思想的文学形式。这部作品,带给我们历史的回望和反思。今天继续连载吉林省作协会员于海涛的作品《辉发河传》……
作者简介:男。汉族。籍贯吉林省辉南县。原长春北郊监狱子弟中学教师、民警。现就职于吉林省监狱管理局监狱工作协会、监狱工作研究所、吉林新生报社,任编辑、记者。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长春作家协会会员、长春市文学社团协会副秘书长、吉林省全民阅读协会理事。近年来在《新文化报》、《长春晚报》、《东亚经贸新闻》、《城市晚报》、《吉林新生报》、《春风》、《参花》、《绿野》、《黄丝带》、《中国文学》、《文坛风景线》、《上海警苑》、《江苏警视》、《监狱工作研究》等报刊发表短篇小说、通讯、论文等近百篇。数次参加全国监狱系统理论研讨,《论监狱亚文化对罪犯矫正之负面影响》、《后现代语境下监狱文学现状剖析》等论文分别获得全国一二等奖。年11月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描写当代监狱民警爱情生活的长篇小说《辉发河传》。年11月出版“一百位感动中国人物——双百人物丛书”之《马海德》。年《辉发河传》获长春文学奖铜奖。
于海涛/文
第四章古怪的场院
场院在村子东头靠近河边不远处一块平坦的台地上。为过去打牲乌拉旗丁收取存放东珠、貂皮、人参、松子等山货供品的院落。后来被大地主汪汉荣重新翻盖,加高加厚了围墙,四角设置了炮楼。为辉发河谷著名的响窑,一报号小傻子的土匪曾经两次攻打都无功而返。土改后成为辉发河公社的大队部,后来改为大队堆放生产工具的仓库。场院不过是推倒围墙后闪出的院坝,而且只在秋季堆放收获的粮食等作物。院心是一颗老柳树,枝干虬曲,足有上百年的树龄。场院的南面是一座高高的稻草垛,一看就是多年积存的老稻草了,乌黑发霉,远远的传出一股浓烈的霉味。这些老宅子为标准的满族四合院,足有近百年历史了,乌黑的瓦缝隙里长满青草和绿苔,门和窗户是镂花的,依稀留下旧时的辉煌,房屋举架较高,雕梁画栋的,充满了古旧的气息。门廊左右遗有上马石,梁柱上油漆剥落,看上去最少也得五六十年了,但大部分保存都还完好,共有十几间。静静地矗立在青山绿水间,仿佛一群垂暮老者背倚青山,对着滔滔东去的辉发河水述说着往事的沧桑。门前立着一根九尺高的索罗杆子,上顶锡斗。围墙残破不堪,整个院落古旧的气息弥漫。过去这里曾经做过大队部,后来大队部迁走了。这里就闲置起来。但居住设施都还可以,老德泰为明仁一家选的是一间向阳的正房,宽敞明亮简单收拾收拾就可住人。房子虽然旧点,但设施较全,有火炕有水井。后院小山一样大量的稻草随便用。
明仁看这么大一个院落都归自己一家来住都未免觉得太过奢侈,除了旧点以外一切都很满意。现在这种情况也只能暂时在这里对付几个月了。但这口窝囊气不能这么轻易就咽了,他一定要找个评理的地方。
望着心事重重的丈夫,淑兰怕他郁闷,一个劲儿地安排他干这干那,让他忙碌起来,省得想那些不快的事情。
老德泰和宗英也想着法儿逗明仁开心。
孩子们没有愁事儿,大人们在收拾屋子,他们已经开始各个屋子厮疯打闹玩捉迷藏去了。
曹大叔帮着卸完车,几乎连水都没喝一口,就急着忙着要去煤矿装煤好往回赶路,他要趁天黑前和那帮外地来拉煤的车老板儿们一齐搭伙走公路了,用他的话讲,叫爹也不再走野狼沟了。过去多少年也没有任何一个车老板儿敢独自夜闯野狼沟。
“虎啊,太虎啦。大半辈子白活啦。哎呀,说出去会让人笑掉大牙的,怎么能干这蠢事呢,虎,真虎!”老头儿一个劲儿地后怕,后悔得直拍大腿。
明仁心里十分过意不去,苦于刚搬家没法做饭,忙跑到乌兰屯里的供销社买了几根麻花和两瓶汽水给曹大叔带着,路上饿了好垫巴垫巴。曹大叔是又摆手又摇头,说啥不要,非要给孩子们留下。在明仁两口子的再三要求下,才勉为其难地收下了。
临走,曹大叔憋了好几憋,终于把明仁悄悄叫到一旁,一脸不自然唯唯诺诺地要明仁帮忙办一件事。
“你看,你看,大侄子……”,曹大叔一个劲地搓着他那双握了一辈子大鞭杆子的手,不知咋的竟口吃起来,“你大叔临走想托你办件事,不知中不中?”
明仁昨晚上山时就看出这老头喜欢他那颗夜明的毛主席像章,二话不说摘了下来,递给老车把式。
老曹急忙拒绝,“不不,你大叔没糊涂到那份堆儿上,这像章一定是谁送你做念想儿的,我老家伙可不能夺人所爱,高低不成。”
“大叔,这像章一般人还真淘弄不到,听说限量发行,全国也没有几个。是我的一个老首长转业时送我做纪念的,你要喜欢就拿去戴吧。”
“不,不是我戴,也是给我儿子金宝戴,那小子老稀罕这玩意儿了,就是淘弄不着,你想想,一个屯二迷糊,有谁能搭理咱呢?假如不是这次搬家,我曹瘸子怎么能攀上你明仁这棵高枝儿啊?看来,我还得感谢昨晚那群狼呢,哈哈哈,你说是不,大侄子?”走南闯北的老车把式边摆弄着像章边偷眼观察明仁的脸色。
劫后余生的明仁笑了,发自内心地道:“大叔,有事您尽管吱声,看在您昨晚帮我们一家子夜闯野狼沟的份上,只要我明仁能办到的,再难,头拱地,我也给您办喽。”
“那好。”老曹这下心里有底了,脸不红,也不口吃了,道:“就是吧,那啥,我已经老天拔地,死么喀嚓眼了,不说啥了。可家里你金宝兄弟就羡慕你们穿工作服的公家人,做梦都想离开咱那个土坷垃地方,这不,这两年正赶上你们矿上招工,临来时跟我说,也想到你们这儿混身工作服穿穿,不知大侄你能不能帮大叔一个忙。”老曹为了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临了又补充一句“大叔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假如是丫头蛋子,我他妈一点都不管。”
“这……”明仁迟疑了。他知道,那曹金宝今年已经二十四了,年龄超了。
“你是寻思那啥吧?没事,大侄。”曹大叔看出明仁的迟疑神色了,他这次是有备而来,忙道:“金宝年龄超了不假,但公社那边我已经找妥人了,户口上的岁数能往小了减,公社那边早改完了,现在,就等你这边一句话了。”
“哦……”原来是早有准备,不愧是走过南闯过北的老车把式,明仁打心眼里佩服这位老农的精明。既然对方诚心诚意想来乌兰煤矿,自己必须将矿上的情况向对方做个说明,于是道:“这煤矿工人可辛苦哇,绰号煤黑子,而且还有危险,三块石头夹块肉,井下作业还是三班倒,金宝能吃得了这个苦?我听说他在家里还学了点手艺,是个半拉木匠,在农村不是挺好吗?”
“金宝说了,只要能不在土里刨食,再苦再累他也能受,再说他是个啥破木匠啊,学了两天半,舞舞揎揎的糊弄老百姓还可以,做个板凳,腿儿还得后找平,一年到头多数时间都是和一帮二流子在一起鬼混。这小子脾气躁,动不动就和人干仗,还好摸枪动刀子,弄不好早晚得出事儿,我都愁死了。”
“您老就这么一个儿子,舍得?”明仁打断他的絮叨。
“舍得舍得,另外,我,我也犟不过这个小鳖犊子。”
“那好吧,如果这样的话,这边我尽量给你办。”了解完这些情况,明仁也只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曹大叔看明仁答应得不是十分肯定,心里未免有点不落底,道:“别‘尽量’啊,大侄子,这么多年了,大叔可就求你这一件事,你可千万给当个事办,这过码儿咱爷们儿后补。”
听到最后一句话,明仁脸色有些不悦了,道:“老曹大叔,啥过码不过码的,说这话你就见外了,也错看我明仁了,乡里乡亲的,谁求不着谁呢,我既然答应了你,天大的困难,想方设法我也给你办到,不冲你和我妈家多年的老邻居,单冲昨晚陪我们全家夜闯野狼沟的份上,咱爷俩就啥也不用说了,你回家告诉金宝兄弟,等信上班吧。”
“好!这爷们儿,不愧当兵回来的,爽快!”老曹大叔高高兴兴赶着大马车走了。
帮忙收拾完屋子,老德泰和宗英领着格儿也要走了,临走前对明仁嘱咐道,“明仁啊,就在这里对付几个月,等那家伙滚犊子了就搬回去。不过,在这里住可是住,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你就权当什么也不知道,另外,也别信那帮老娘们儿们的胡咧咧。”
“嫂子你胆子不小吧?不行的话等明仁大哥值班了我领格儿过来陪你做伴儿。”宗英一脸的顾虑。
“不怕。过去在老家我一直一个人领俩孩子过,啥也不怕,你们放心吧。何况现在你大哥天天在家呢,没事。”
“那就好。那我明天早晨过来看你们。”
老爷子刚要走,大家却忽然发现林湘不知道哪里去了,刚要找,孩子自己回来了,说是找地方拉屎去了,大人也没有深究。
其实,刚刚这小子抱着装狼崽的那个木头盒子到梁兴周家去了,趁人不备爬到了房子屋顶,把那个木头盒子悄悄放到了烟筒根儿下面。他想起老德泰爷爷的话,狼是报复性最强的动物,母狼不找到小狼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看来有这只小狼,就可以乖乖地将抢占房子的梁兴周一家撵走了。
一家人折腾了好几天,加之昨夜野狼沟连惊带吓都累坏了,所以当夜简单吃了点饭早早就睡下了。
然而,半夜明仁却被一阵奇异的声响惊醒了,一睁眼,发现淑兰也醒了,正睁着大眼睛惊恐的望着自己。
声音来自西屋,真真切切。
“别怕,我出去看看。”
“那你小心点,拿点家伙什儿。”
“没事。”明仁说着点燃蜡烛拉开房门走了出去,顺手摸起了一个立在屋角的弯头木棒。外面院子里很静,月光如水地泻下来,远远地听到辉发河流水的声音,哗哗一浪一浪地传来,很好听。西屋早已无人居住,堆满了破破烂烂的杂物,门窗也破烂不堪。明仁拉开房门,那奇怪的声音似乎女人细声细气的在哭,同时伴着山风吹过窗户破洞将塑料布吹得“呼啦啦”作响。
“谁啊?出来!”明仁仗着胆子吼了一嗓子。无人应声,明仁暗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是自己吓唬自己啊。他打了个哈欠,端着蜡烛转身往回走,但就在他一转身的瞬间,分明看到一条黑影越过洞开的北窗,踉踉跄跄向北面的后山岗跑去。
“谁?站住!”明仁绕过地面上的破烂家什,几步追到北窗,顺手将手中的弯头木棒子扔了出去,弯头木棒带着“呜呜”风声一下子砸在那家伙后背上,那家伙“嗷——”一声惨叫跌倒在草稞子里,可见砸得不轻。这种棒子叫“布鲁棒子”,是关东满族人草原上打兔子的,威力极大。明仁今晚纯属误打误撞。那叫声很痛苦,明仁怕把对方打死,跳窗追了出去,只见窗外半人高的青草丛生,荒草萋萋,山风飒飒,什么也没有了。
那家伙跑得好快。但愿没有把他打坏,明仁只不过是想教训教训对方。
随着那家伙的一声惨叫,后山梁子上一双绿荧荧的鬼火也消失了,同时伴有一声呜咽似的狼嚎。
回屋后,淑兰紧张地追问:“什么声音?看见东西没有?”
“没有。大概是耗子嗑东西,快睡吧,明天早起还得收拾房子呢。”怕淑兰害怕明仁没敢实话实说,轻描淡写地搪塞过去了。
淑兰将信将疑,迷迷糊糊睡下。
明仁心里有事却再也睡不着了,听着窗外隐隐传来的河水声音,半年来的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让他说不出来的压抑。
“啊,啊啊啊……”儿子林湘从火炕的另一头传来痛苦的压抑声。
“怎么了,儿子?醒醒,快醒醒。”明仁坐起来,叫醒儿子。
这孩子大概是尿憋的,所以梦魇住了。果然林湘爬起来到门口尿了一泡长长的尿,回来接着睡了。
明仁也慢慢睡着了。
早晨一睁眼,淑兰忽然发现睡在炕稍的林湘不见了,急忙推醒明仁。明仁没当回事,嘟囔着说,“尿尿去了吧,没事。”接着继续睡。可等了几分钟仍不见孩子回来,淑兰可沉不住气了,披衣下地,推门出去,不看不要紧,一看下了她一大跳,尖声叫了起来,“他爹,快出来,儿子这是怎么了?”
明仁一惊,睡意全无。出门一看,只见太阳已经升起一竿子高了,山间薄雾缭绕,林中各种鸟儿在婉转鸣唱,空气湿润的很。儿子林湘光着小屁股一丝不挂地睡在院子里那棵老柳树下,满面潮红。
两口子急忙奔过去,一迭声地摇醒儿子。
“爹,妈。”林湘揉着眼睛坐了起来,“我这是在哪里啊?”
“呵呵,没事,你小子睡毛楞,梦游了。”明仁轻轻给了儿子屁股一巴掌,问淑兰:“这孩子在老家也有梦游的毛病么?我好像没有听说过呢。”
“没有啊,从来没有。都是搬家搬的,加上这两天吓的。早知这样不如不搬了,大人孩子不得安生。”淑兰不知不觉抱怨起来。
明仁不高兴了,口气明显带着不悦,“那你就一个人再搬回去,我们爷儿几个单过。”说着他哈腰抱起了儿子。一摸吓一跳,孩子浑身滚烫,“哎呀,发烧了。”
看丈夫表情有异,淑兰不再抱怨,急忙帮助丈夫把儿子抱回屋。吃退烧药,用白酒搓身子,忙活了一早晨,才把烧降下来。
老德泰领着格儿八点钟过来时,两口子刚刚喘口气,忙得早饭还没有吃呢。
淑兰沉不住气把昨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老德泰,明仁也告诉了他看到了跳窗的那个黑影。
老德泰说,“没事,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们不知道,在你们之前半个月,小学校的汪老师领着孩子也在这屋住过,刚刚搬走。汪老师长得漂亮,煤矿一些不三不四的家伙和屯里的一帮二流子就有事没事装神弄鬼的总来捣乱。可能昨晚误以为那娘俩还没有搬走,继续来吓唬她们的,不用管他们,被我抓住,我把他们腿打折喽,看这帮兔崽子还敢得瑟不?”可对林湘的梦游他也奇怪,“按理说不会啊,大概这孩子是因为惊吓过度造成的,没有两下子谁也不敢闯野狼沟,这毕竟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接着他又检查了一下孩子的伤口,伤口已经结痂,但青黑依旧,老德泰的眉毛扭成了一个疙瘩。他知道,这孩子百分之百中了狼毒了,这病几乎不去根儿,在体内一藏就是十几、二十年,发作起来恐水,怕光,见谁咬谁,六亲不认,最后病人只能在笼子里孤独地死去。其实就是狂犬病,老德泰知道这个意思但说不出来这个名字。可现在又不能明说,那只会加重孩子父母的心理负担,于事无补。只说孩子可能冲着什么了。他那晚的草药是治疗红伤的,但却不能解毒。只能寄希望于侥幸了,万一将来这孩子没事岂不是更好。
白天,大人们在收拾房子,孩子们又疯闹了一天。傍晚上老德泰走时嘱咐明仁两口子继续观察,有情况随时去屯子里找他。他大哥韩德重今天刚好有事情出门了,等他一周后回来给孩子好好看看。韩德重是乌兰屯里的韩姓穆坤达,也是远近有名的大萨满。不过,老德泰没有告诉明仁两口子,只说他会治病,专治小儿惊吓。
明仁和淑兰千恩万谢,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儿子的病有多么的严重呢。只以为不过是惊吓导致的发烧。
半夜里林湘继续发烧说胡话,而且比昨晚还严重。这孩子是怎么了?明仁两口子忧心忡忡。窗外山风吹动窗户上的塑料布呜呜作响,辉发河水哗哗一浪接着一浪传来,后山梁子上的狼嗥清晰地传了过来。更加重了两口子的心事。这个家搬的啊,还不如在老家安安稳稳过日子了。又是一个没注意,林湘早晨又睡在了院子里。
两口子大惑不解。淑兰觉得可能如老德泰所说,莫非这孩子真的冲着什么了?
明仁打死也不信那些神了鬼了的。上医院,接诊的是院长严家骥,是明仁的好朋友。听完情况,立刻给明仁一顿训,直骂他无知,拖了这好几天才来看病。他嘱咐护士立刻给林湘注射了一支当时极为稀缺的青霉素消炎。然后郑重告诉明仁需要他去长春买治疗狂犬病的特效疫苗,那疫苗只有长春市生物制品研究所独家生产和售卖。明仁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他搬家已经请了好几天假了,不能再耽误工作,再说,当时人们对狂犬病的认识也不是很深刻,没有太当回事。严院长说,我可告诉你明仁,现在不打疫苗,将来这孩子有什么一差二错你可不要怪我。明仁说,你们医生一贯喜欢小题大做,我这儿子不至于点儿那么低吧。老严说,但愿吧,一般人大都是没事,不过就怕万一。
此事十余年后被严院长不幸言中。
中午回家时,路过自己家门口,明仁绕路而走,他怀着一腔的愤懑,无处发泄,拳头都快捏出水来了。
天气很好,晴朗无云,老柳树下聚集了几个当地装束的家庭妇女在纳鞋底,都穿着满族的斜襟大夹袄,梳着疙瘩髻,叽叽喳喳说着屯子里的家长里短,不时发出一阵阵尖声大笑。看到明仁父子走过了都纷纷噤声,好奇地打量着他们。
明仁友好地冲他们点点头,笑了笑,领着儿子走了过去,快中午了,淑兰还等着爷俩吃饭呢,下午自己一定得上班去了,单位还一大摊子事儿呢。
可走过去没几步,后边就有人叫自己,“这位大兄弟,是矿上的吧?”
明仁只好停下脚步转回身来,“对啊,你们怎么知道?在做鞋啊。”
“看衣裳!社员哪有穿军装的,哈?”搭话的女人三十多岁,精明利落,一双大圆眼溜来扫去,骨碌骨碌直转,“是谁介绍你们来场院住的?那怀孕的是你老婆吧,挺俊的,哈?”
明仁笑了笑,“是老德泰大叔介绍来的,我们矿里分的家属房出了点差头儿,暂时在这里借住几个月。”
“这老头,不用说,我一寻思就是他。热心肠归热心肠,可怎么能往场院介绍啊,这不是坑这家人么,哈?”
旁边一位五十多的壮实大嫂瞪了一眼大圆眼妇女,道,“别多嘴。李八歌,小心老德泰那老爷子骂你啊,场院怎么了,场院不是人住的啊?”
李八歌叫李桂琴,白白净净,大眼睛、薄嘴唇。五年前从山南嫁到辉发河公社,嫁给当时的农民李大炮,因为腿快嘴更快,人送绰号李八歌,大名却没有几个人知道了。李八歌边把大马蹄针在头发上蹭边反唇相讥,“好心是好心,场院咋回事你不知道还是我不知道?那汪老师娘俩前两天是怎么走的?哈。骂我我也得说出来,虽然老爷子是好心,但咱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家子往火坑里跳不管啊,是不是,哈?”她转头对一头雾水的明仁爷俩说,“你们一家在场院刚住吧?再住两天赶快搬走,这房子有说道儿,犯邪。再住,恐怕对大人孩子都不好,哈。”这女人冲谁说话都带着个反问句“哈”。眼珠像轴承里的滚珠儿一样转来转去。
“就你嘴欠。”其他妇女集体数落李八歌。
“犯邪,犯什么邪?”明仁更加疑惑。
“就是闹鬼呗,还非得明说。”李八歌白了明仁一眼,不吐不快,说完长长出了一口气,仿佛这番话她不说出来就得憋坏一样。
“胡说吧你就,看老德泰怎么收拾你。”
明仁笑了,说“哦,是这么一回事啊,谢谢大嫂,没事,我是共产党员,不信鬼神,放心吧,再说这两天也挺太平的。如果没有什么事,我还有事,先走了啊。”说完拉着儿子回家了。
身后,远远传来妇女们的哄笑声,“哈哈哈,李八歌,叫你多嘴,碰一鼻子灰吧?你这是看上人家小白脸了,借由子没话找话呢,活该,看你还敢撩骚不?让你家爷们儿知道,不打你个满地找牙才怪。”
“你,还有你们,埋汰我,哈?看我不撕烂你们的破嘴,你们就没有动过歪心眼啊,哈?乌鸦落老母猪身上就看到别人黑。没有一个好东西。”李八歌舌战八方,毫不怯阵,几个妇女嘴说不过她便动起手来,嬉笑打闹,乱作一团。
淑兰从窗户远远看到明仁和那些大嫂子们搭话,待得丈夫进门就问怎么了。明仁说没事,几个家庭妇女在扯闲话呢,接着把儿子的病情简单对淑兰说了说,怕引起妻子担心,他也就没把严院长交代的话告诉她,再说他自己也没有当回事。不明就里的淑兰也就放下心来。
然而,到了夜里,林湘依旧发烧说胡话,梦游的频率也增多了,上树噌噌的跟猫一样也摔不着。白天却蔫蔫的,一点也打不起精神来。
这孩子是怎么了?眼见得越来越大发了。
明医院,可这次严院长也搞不明白了。建议明仁不行的话就住院观察。
不行啊。明仁一声苦笑。不是不心疼儿子。自己要天天上班,家里淑兰挺着个大肚子,还要照顾林红。林湘住院了怎么护理啊?再说这孩子除了发烧外也没有其他症状,看不出所以然来。最后决定还是回家观察。
当天晚上下班后回到家里,明仁看到了那天搭话的大嫂李八歌正在自己家的炕头上和妻子淑兰指手划脚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看到明仁进门,李八歌立刻噤声,抬屁股蹬鞋下地一溜烟地出门走人,边走边说,“大兄弟大妹子啊,信不信由你们,哈?嫂子我可是一番好心哪。好了我走了啊,家里你们那还愿的死鬼大哥还等着我做饭呢。”随手拿走了一个小包,里面装着淑兰送她的那张狼皮。这狼皮淑兰一看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望着李八歌远去的身影,明仁一脸的不高兴,刚要发火。但一看淑兰,竟然面白如纸。“你这是怎么了?李八歌和你说什么了,吓成这样?她的话你也信,农村妇女扯老婆舌罢了。”
“看来那天你们爷俩就听说了,就是瞒着我不告诉我是不?”淑兰快哭出来了。
“什么啊?胡说八道的话你也信。不告诉你是怕你瞎担心。哪有什么鬼啊神啊的,就是自己吓唬自己。”明仁辩解道。
“按理说我也不信那一套。可咱儿子不是冲着啥了,怎么能发烧不退呢?这都一晃儿多少天了啊。这房子还是有说道儿,要不那学校姓汪的老师怎么搬走了呢。今天李嫂说,房后就是乱葬岗子,半夜看后山全是鬼火,门外那稻草垛里黄皮子老鼻子了,老多年了,都成精了,经常出来迷惑人;这屋里还吊死过地主家的姑娘呢,还说,过去有不少人亲眼见过那姑娘的鬼魂在房子里飘来飘去的,白衣长头发,红舌头有一尺长。还说这场院过去狼从来不敢来,可最近几天天天夜里听见狼嗥,屯子里的鸡都丢了好几只了,百分之百是被狼吃的,狼就是咱儿子招来的。大伙老有意见了,说下一次狼就开始吃小孩儿了。妈呀,吓死我了,这房子我可不住了,我不敢住了,再说还有俩孩子呢,可怎么办啊,呜呜。”说道最后,淑兰快哭了。
“滚犊子!少听他妈的李八歌瞎白话,再来妖言惑众吓唬人我就找她家老爷们儿算帐去。再说,哪座老房子不死人?哪座山包子不埋人?听她那么一说还完了呢,听喇喇蛄叫还不种地了呢。我林明仁就这么大能耐,只能给老婆孩子这么个破地方容身,再说,这话传出去怎么给老德泰大叔交代,说他找了一座凶宅给我们一家人住?老爷子会怎么想我们一家,你对得起老爷子的一番苦心么?”明仁气坏了。
淑兰知道自己做错了,没有争辩,可打心眼里还是划魂儿。那李八歌今天进门时目光诡异神情怪诞,张口就问,
“你家住在这院子里没什么事发生吧?”
“没啥大事,就是不知道谁家的姑娘半夜老哭,我的儿子也梦游。”
李八歌说:“对了。快搬家,快搬家,搬晚了会遭来横祸的,对大人孩子都不好,哈。听嫂子的,我就在这屯里住,好多年了,姓李,不会坑你们一家子。”然后蹁腿上炕吧嗒着小烟袋和淑兰着力整整渲染了一下午这座老宅子的凶险。
这座打牲乌拉旗丁当年的官衙后来被一汪姓地主改造成四角带炮台的宅院,民国时期因为婚姻问题的确那家地主的二小姐因为要和来“砸窑”的胡子私奔,里外勾结未遂被家人发现,无奈只好在东厢房里吊死了,从那以后经常听到半夜有人呦呦在哭。土改期间分给了农民,住了几家都不到半个月就纷纷逃离。有个外来户李铁匠不信邪,就是那李八歌的叔叔,非要住进来。结果第二天就中风了,瘫在炕上窝吃窝拉一整年,满口呜呜咦咦,临死前还用手指着这座院子唔唔不知所云。以后常年无人再敢踏进这座院子半步。偌大的一个院落只好做了场院,用以秋天社员打场用。
对李八歌说的这些淑兰入耳入心,这几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让她不得不信以为真。最后直吓得她面白如纸,浑身打颤。那张狼皮也送给了她,贪心的李八哥没有想到后果,这才导致了她家所有的鸡当天夜里被狼咬死。
“我不是自己怕,我都是为了孩子们着想。”
“少拿孩子们打掩护,别扯那立根棱儿(东北方言,扯淡意)。”
两口子都怄起气来。明仁连晚饭也没有吃,倒头睡下了。半夜里他被淑兰猛地推醒了,只见淑兰浑身抖成一团用力地往自己怀里钻同时紧紧搂着自己的脖子,带着哭音大叫,“快听,西屋有人哭!”
果然,西屋传来女人气若游丝的哭声。明仁一惊,“嗖”地坐起来。刚一坐起来,那哭声又突然改成了笑声,更加令人毛骨悚然。这时,更加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小林湘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开门就要往外走去。
“儿子,你干嘛去?”
林湘并不理会爹妈的呼唤,丢了魂似的继续往外走,走到院子里那棵老柳树下三下两下就爬了上去,身手异常敏捷,然后又迅速爬了下来,在树下倒头就睡。
明仁下地随后追了出去,光着脚连鞋都没有来得及穿,眼前发生的一切不由使他惊恐万状,毛骨悚然。人最怕的是被不熟悉的东西所惊吓,纯属护孩子的本能使得他不顾一切追了出去。等把儿子抱回屋内,他才发觉浑身水洗一般,早已出满了冷汗。
后山梁子上依旧时而传来一声接一声悠长凄厉的狼嗥。
李八歌说的没错,看来这房子真的有说道儿,的确犯邪。
当天夜里同时发生了公社的羊和李八哥家鸡被咬死的事情以及梁欢见到狼挠窗户的恐怖事件。这都是那条母狼在进行疯狂报复。乌兰屯已经好多年没有狼群来骚扰了。这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林湘父子与狼结下的梁子。村子里的狗也疯狂地叫了一夜。但住在远离村庄场院的林家并不知道发生的这些事情。
两口子一夜没睡,大眼瞪小眼,无计可施了。儿子百分之百是冲着啥了,否则无缘无故怎会半夜高烧不退,怎会无缘无故半夜梦游上树?
上午,听完明仁两口子对这几晚情况的讲述,老德泰吧嗒着旱烟管半天没有出声。白天,林湘又恢复了健康,没事人一样和格儿林红她们玩捉迷藏去了。西厢房里传来孩子们欢快的笑声和吵闹声。
老德泰重重地打了个嗨声,长叹一口气,用鞋底将烟袋锅里的烟灰磕净,想说什么,张了张嘴,终于没有说出来,又点燃一锅烟“吧嗒”起来。
明仁急坏了,迫不及待地说,“大叔啊,要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打死我也不信,可事情真真切切明摆着啊,我不得不信了,我得为这娘几个负责啊,您老人家帮忙帮到底,帮助我们重新租个房子吧。”
老德泰瞪了他一眼,“要能租我早给你租了。现在屯里的闲房子都被你们这些煤矿工人租没了。你管招工的,你说说你自己一个人这几年就招进来多少人?没有一千也得八百了吧?还有那些当兵转业的、学校毕业分配的等等,这么小个地方一下子涌进来好几千人,哪能承受的了?这房子啊,没有李八歌那娘们儿白唬的那么邪乎,不过,说道儿还是有的,可是,我老头子没有资格告诉你们啊,看来非得我大哥韩德重出面不可了。”
“嗯?”对老德泰最后冒出的那几句“官话”,明仁两口子面面相觑,大惑不解。
“等着吧。我去把我大哥找来。他是这一左一右的神医。除了孩子的病,一会儿啥也不许问,啥也不许说。只能听。”说完,老爷子诡秘地笑了笑,抬腿走人了。
半个小时后,老德泰回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位瘦高的老者,装束与当地山民无二,但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与众不同的精神劲儿。
一个照面,明仁就觉得这老爷子不陌生,忽然,他想起了,这位就是那晚在哈达岭击鼓的白衣老爷子。虽然那晚在山顶上没有多少月亮看不太清楚,而且大家转瞬即逝。但老人家的举手投足还是让他一眼认了出来。
看着明仁惊讶的表情,老德泰笑了,道,“我来介绍,这是我大哥韩德重,咱乌兰屯的老韩家的萨满,我们满族话叫穆坤达,就是头儿,有什么事情都得先请示他。明仁,你现在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求救于他。”
瘦高老者一眼看出明仁认出自己了,也不做隐瞒,爽朗地道,“没错,明仁大侄子,那晚在山上的确是我。外乡人不懂我们山野规矩,三言两语一时也解释不清楚。你们的情况我二弟德泰都告诉我了,这个世道,好人难做啊。不过,没事,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既然来了就是缘分,听说你们家在叶赫那疙瘩也姓韩,我们韩家有一股的确在叶赫那边失散了,家谱上有,论起来我们五百年前是一个老祖宗,而且你和志成还是多年的战友,那我们就是一家人啦。我们老哥俩会尽全力帮助你们,有我们吃的就有你们吃的,有我们住的就不能让你们一家老小住露天地儿去,放心吧。”
明仁面露难色,重重地叹了口气,“德重大叔,现在问题是这房子无法再住下去了,扰得大人孩子不得安生,尤其是林湘,天天半夜发烧梦游,过去在老家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我和他妈都愁坏了。”
老德重和老德泰哥俩目光碰了碰,彼此会心地点了点头,刚要开口说话,就看见几个孩子野马一样冲了进来,格儿边跑边叫,“给我,快给我,爷爷不让动的,会骂死你的。”
“不给,不给,就不给。老道老道,谁捡谁要。”林湘头戴一顶缀满流苏奇怪的帽子,脖子上挂一面铜镜,腰缠一串哗哗作响的铜铃横冲直撞闯进来,边跑边将手中拿的单鼓一顿乱敲。
明仁还没等做出什么反应,老德重哥俩却双双同时跳下地去,尤其老德泰,疾言厉色一把抢下单鼓,大喝一声:“兔崽子,放下!反了天了,老祖宗的东西也敢动!”
两口子还从没见过老德泰发这么大的火呢,同时都愣住了。老德泰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尴尬地解释,“这小子太淘气了,别的东西都可以动,唯有这些东西不能动,有说道儿的。大哥,给你。”
对满族人来说,有些东西是永远不许碰的。例如西炕不许坐,装在口袋里的佛多妈妈不许看等等。而初来乍到的林家人哪里知道这些禁忌。
老德重接过单鼓,目光炯炯地盯着林湘,一声也不吭。
淑兰不知儿子又闯了什么祸了,急忙赔礼,“大叔,您二老消消气,别和孩子一般见识,这小子让我们操老心了,一会儿让他爹收拾他。”
“啥一会儿啊,现在就来,给我过来!”明仁挥手就打,被老德重一把抓住。没有理会明仁,继续目光炯炯地盯着林湘,和蔼地问,“孩子,你喜欢这鼓?”
林湘点点头,丝毫没有害怕的意思。
“你从哪里找到的这鼓?”
“西屋天棚上我们藏猫猫找到的,还有好多别的东西呢。我都没有动,喜欢这鼓就拿下来了,老爷爷,你要喜欢就送给你吧,我再上去取,反正还有好多。”眉清目秀的林湘瞪着天真的大眼睛道,同时胆怯地扫了一眼旁边冲自己运气的父亲。
“哈哈。好孩子,还要把鼓送给爷爷,好,好孩子。你会敲鼓么?敲两下给爷爷听听。”说着老德重把鼓交给林湘。
“大叔,不能惯着他,这小子……”
“不,就让孩子敲。别拦着他。孩子别怕,敲,放心大胆地敲,让两位爷爷和你爹妈都听听。”
望着老德重爷爷和蔼的眼神,林湘不再有顾虑,放手敲了起来,嘭,嘭嘭,嘭嘭嘭嘭嘭……
鼓声响起,声震屋宇。小林湘越敲越起劲,越敲越兴奋,慢慢进入迷幻状态,同时摆动腰肢,脚踏鼓点,满屋子转起圈来。
“哎呀,好!好……”老德重忘我地拍手大叫起来,眼角蕴泪,“哦亢阿塔穆坤后继有人了啊,感谢老祖宗啊!感谢老祖宗!”
明仁和淑兰都倍感奇怪。
中午,老德泰哥俩都没有走,明仁让淑兰张罗俩菜又买了二斤酒留他们俩吃饭,席间,明仁对近日发生的一切,这时才恍然大悟。
经典回顾
连载:辉发河传——第三章房子风波
连载:辉发河传——第二章哈达岭惊魂
连载:辉发河传——第一章夜闯野狼沟
连载:辉发河传——内容简介
听过客那一曲长歌——读《百年苦梦》
《恩存文化》 如果有想与大家分享的好文章也可以发送至
qq. 最近本平台邀请了专业的发现文章并肯花功夫整理这些文章的读书人。突然之间,本平台就丢了任何一种激素类鸡汤,开始发表了深入的极具思想性的文章。凡是能够看懂这些文章的,都是具有深度思考的朋友,也因如此,一大批优秀的作者也就踏足本平台。感谢你们的支持,如果想让你的朋友与你一样优秀,请转发给懂得的人……萨满文化家族传承
赞赏
人赞赏
白癜风有什么好办法北京白癜风是怎样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