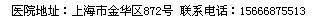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舌系带短缩 > 相关医院 > 行走一座岛,穷尽孤独
行走一座岛,穷尽孤独
静静做自己,让世界发现你
整理文件夹,发现自己也是拍过照片的人!所以有了这篇游记。
文字偏长,它可能不讨喜,但是,充满诚意.......
一座岛,穷尽孤独
——记东极东福山
前因年时,因为心情低落,想去东极呆几天。当时的东极“养在深闺人未识”,渔业发达,原住民年龄结构大致合理尚且安居乐业。不便之处是住宿餐饮要托朋友代为安排,由乡政府招待所之类接待的。委托的朋友大概怕我想不开,列数岛上种种不便,结论是“不值得去”。
这一失之交臂,就是十三年。期间有无数次机会,动过许多次念头,但也更多的理由阻扰成行:比如坐船时间太长,万一晕船;比如夏天蚊子太多;比如听说东极的物价越来越高了,性价比不高;比如海岛都大同小异,没必要非得去……
这期间,东极原住民中的年轻代不断外迁,继而旅游业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发展,年底,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在东极开拍之后,终于有了爆炸式突破,旺季时开往东极的航班一票难求,游客在售票处彻夜排队,票贩子应时而生,小岛物价高企……另一方面,与日益增加的游客数量相比,岛上接待能力有限,家庭宾馆设施因陋就简,环卫配套薄弱导致垃圾污染触目惊心……网络评价毁誉参半。
当“10岛计划“排上日程,东极,理所当然地列为第一站。再不去就老了呵,岛老了,海老了,我也老了……
时间:年3月15日周日
气象:阴,有雨
海途乍暖还寒,连日阴雨,不是游海岛的好季节,更不是上岛的好天气。但是计划太久,终于按捺不住,等晴天等空闲等万事俱备,不如想到了就出发。你饱览东极山丽水秀、海晏河清的明媚,我不妨去领略一番凄风苦雨、荒山僻径的幽趣。
东极轮上寥寥数人,游客模样的不过五、六位,天不作美,穿了雨披在甲板上小站片刻,但见混沌一片,无可名状。
船行一个小时后开始颠簸,前座小情侣模样的年轻人传出呕吐声,此起彼伏。不久,我邻座和后座的女士也加入呕吐行列,其声连绵,如同吐出一座又一座完整的山丘。忍无可忍,我终于也吐了。至此,东极岛民与游客的界限泾渭分明:一边安之若素,一边人仰马翻。乘务人员早已司空见惯,面无表情地继续分发垃圾袋。新袋到手,一干人如领圣谕,换个姿势再吐一次,如此和盘托出,直到胃囊空空如也。这才缓过神来重新做人。
而船也即将到达,目的地庙子湖的准备上岸,前往青浜和东福山的旅客则早有“东福轮”侯在船侧接应。行前听原籍东福山的朋友说东福山风景比庙子湖美上“一百倍”,虽则有出于乡土情结的自吹自擂加四舍五入大写意笔法之嫌,但即便刨去九点九折水分,还能翻个倍,所以目标坚定地奔赴东福山。
上得渡轮,空气流畅,视线所及处,大小岛礁均显出卓尔不群面目,海水浅蓝微绿,顿时觉得神清气爽,继而食指大动。就着开水,将一包饼干尽数吞下尚意犹未尽。四十五分钟航程,借机打个盹消除旅途疲乏。再睁眼,长长的防波堤,东福山码头横在面前,穿蓝灰色迷彩服的兵哥哥年轻的笑脸,让人一下子想起“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的胜境。
被船员拎上码头,沿着公路步行百米左右后,上过《国家地理杂志》的标志性白色灯塔,雄阔的圆润的海礁,依山而筑鳞次栉比的石屋群,雾蒙蒙的山头,幽长的石板路,雨雾中,整个湿漉漉的海岛小渔村忽然就劈面扑来。
哦!东福山!
房东夫妻选择这间家庭宾馆原因有二:一是它临海,二楼的房间推开窗就能看到灯塔(我忽略了它的窗户小得简直像梳妆镜);二是在我面对外形雷同的旅馆犯选择障碍症的时候,正好从台阶尽头伸出张黝黑的笑脸(一看就是渔民模样),他用方言很重的普通话,在细雨中无限洪亮地问:“住店吗?”
我仰起脑袋,用方言同样洪亮地反问:“有饭吃吗?”
“有吃哦!”
那还挑什么,就它了!
老板夫妻大概六十出头,看起来像远方亲戚。不需要拿捏分寸,他们脸上浮现的,就是长期生活在狭小孤岛的居民,对外来客的天然热情。
我很快知道了他们来自东极的另一个岛青浜,老板娘是卫生局下派的卫生员,在这里一呆四年。“没人愿意来接替,回不去了。”老板娘有点无奈。两年前造了这幢两层的石头房做家庭宾馆,连装修负债百万,“旅游客人多起来了嘛!老头以前是拖虾船上的,现在年纪也大了,下海太辛苦。儿子一家住沈家门,偶尔来住几天,旺季会来帮忙。这么多债,压力还是蛮大的。”但她脸上没有愁苦。她的脸,只是在说:瞧!这么多岁月都过去了。
我们在的宽阔开间是吃饭的地方,摆了一张可坐7-8人的圆桌,蓝色塑料凳叠成两叠,靠墙一台自动麻将机,麻将牌整齐摊在桌上,老板进门后就在那里独自玩“通关”,不时笑着附和几句,脾气很好的样子。
阴雨天瓷砖地面都是潮的,她一边用脚将大块旧棉布划来划去擦地板上的水汽,随口抱怨着天气,一边问我想吃点啥,“吃饭可以自己点菜,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吃。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没什么海鲜,天还冷。”因为“没有菜“,她圆圆的脸上有歉意,短发烫过,不高的身材略发福。她看着我,这一刻她像我的母亲。
客房乏善可陈。为了追求最大容客量,他们把一间大房子隔成三块,靠墙留条走廊,进门一个小间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一个电视,算单人间。中间是卫生间,洗脸盆坐便器和淋浴间。最里面一间临海,是给我住的,不到10平米,两张单人床夹着小床头柜,床对面老式的电视柜上放着电视机,墙角一只东倒西歪的立式衣架。完了。
我已经说过梳妆镜一样大小的窗了,铝合金的窗玻璃装了两层,防风防水也隔音。窗外就是一览无余的大海,也即是我来时的路,此时茫茫不知所终。
她说人家在开是一百元,你给八十好了。她主动降价,脸上那种表情,仿佛收钱是多么难为情的事。
吃完热腾腾的海鲜面,准备出去兜一圈,一直在玩牌的老板这时站起来问:“你要出去?要我陪你去吗?”我忙说不用,让他继续玩。
他憨笑着搔搔头:“我是没事干随便玩玩。天气太冷,拱淡菜(钻到海底去摘淡菜)还吃不消。”为自己的“无所事事”做解释。
夫妻俩一起送我到路口,指点方向:“环岛的话要三四个小时。走累了就回来。如果过了白云宫就别回来了,往前兜跟走回来的路一样多了。“
老板娘在身后追问:“你会走(远)路么?我们的名片带着么?上面有电话,有事情或者迷路了打电话回来。“
走出几米后,又听到老板用大嗓门喊:“你礁石上不要上去哦!拍照的时候留意脚下,别滑了!“
景·场景东福山是雄性的。干脆利落的山水,方正简朴的石头民居,山上到处都有的巨石群,都是雄性气质。以至于让人忘了山上也会开出艳丽的山茶花。让人忘了也曾有无数个春天,到达过这里。
拾级而上的村路上没有人。一些荒废的石屋,门窗洞开,野草,活过来又死过去。被遗弃的石臼蓄满了雨水,常青藤艰难地攀延上去,停在臼沿,欠身水面,静静地探照自己的影子。我看到了老人,坐在更古老的石屋里,他们闭着眼睛,等待时间风一样过去雾一样过去。跟老人们气质相似的是放养的山羊,洁白、优雅,它们是岛上神圣的生灵,如果你见过它们站在高高的山岩上迎风远眺的模样。放养它们的人去哪儿了呢?远离村庄的乱石堆旁的石屋,难道是他的家?
在无人的石板路上,想象旅游旺季时蜂拥而至的游客,那场景,比虚空更为空荡,比荒无人烟更为荒芜,他们来寻找什么?他们又带走了什么?他们不远千里漂洋过海,来潜入一场沉睡的梦中,将会看到什么?
如果在东福山上等待远行的人归来,真是一种煎熬。随随便便站到某处高地,世界一览无余,藏不住惊喜。“过尽千帆皆不是”的无尽惆怅,千锤百炼,锻造出岸的坚强。东福山的人们,是不是习惯了不再等待?把思念和期盼,托付给海。把匆匆四季日日夜夜,托付给山。
那么,你是从夕阳西下的山坡上一次次离开的么?离开了坚硬的石头房里柔软的妻女、白头的母亲,你是用怎样的背影一次次走出她们的目光?那条离家路上,只有漫山的、发黄的茅草一个劲地扑向你,万箭穿心地催你去:去!去!去!你是否曾回望那个安详的村庄,在转角的地方?还是吹着口哨,义无反顾地奔赴海洋的邀约?那你知不知道,那些日夜弥漫在亲人眼前的雾,到底是从遥远的海岸漫上来,还是从高高的山头沉下去?
时间:年3月16日周一
气象:大雾黄色警报
钓鱼停航。那么是回不去了。码头上不知从哪冒出来的三五个本地人,都是等待离岛的人。
在半山腰经营着一家客栈的老板,是在码头上萍水相逢的人,也是这一天旅程的主角。他们叫他“晾竿”,但是他没那么高,也没那么瘦。或许不叫“晾竿”,只是一个相似的音节,谁知道呢。他大概四十多岁,如果不是留了板寸,就有明显白发了。他的长相,算是斯文的。
每个封闭的小区域里,总有那么几个相对别致的少年,他们未必会是男孩们的首领,却是女孩们的目光四处追逐的对象。他们成年后,大概都会离开,在不知道的世界里成长成平庸的中年人,但他们的脸上,无一例外,残留着少年时被广泛青睐的自信和仿佛阅尽人间的稀松平常。
“晾竿”,应该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一起在灰蒙蒙的码头边钓了小半天鱼。他们帮我扎上冰冻的小虾米做诱饵,教我怎么放钩收线。“你别想着回去了,今天就跟我们玩。”“晾竿”对我说,“下午去我的茶室喝茶。”
两指宽的小石斑鱼不断上钩,三根钓竿,一会儿就钓上六七条。石斑鱼和黑鲷,最小的才拇指粗。
“小鱼不放回去吗?”我问。
“不放!我们放掉别人又会钓走。”他们中看起来内向点的一个说,“鱼儿太笨了。咬过一次钩,放了,还来咬。”
“所以它们是鱼。没脑子!要被人吃掉。”另一个说。
他们把钓竿横在防水堤的栏杆上,从码头边堆放的啤酒纸箱里挖出瓶装啤酒,用打火机开了瓶盖,就着烟喝掉,一边指责啤酒的主人——那个准备在码头边开酒吧的外地年轻人——太懒,“这种天气,再不搬走纸箱就脱底了。”他们说,“招呼一声,我们都会帮他的,一会儿就搬好了。他又不招呼。”
钓完鱼,我们四个人一股脑儿塞进“晾竿”破破烂烂的皮卡车,“先把鱼放你房东家,叫她做着中饭,我们先去喝茶。”“晾竿”对我说。
“XX拱淡菜去了,等会去要点来。”内向的年轻人说,“要一盆来炒着吃。放点生姜。”
“没有比炒淡菜更好吃的了!”“晾竿”说着踩一脚油门,车冲上缓坡,在盘山公路上蛇行。岩壁上,半空中,大片的仙人掌山一样压过来,又被我们甩在身后。
往事“晾竿”的茶室,是搭在半山废弃营房旁的简易建筑,一整间足有七八十平米。八、九套藤桌椅都是旧货市场淘来的。天花板上垂着五颜六色的塑料花,墙角堆着冰箱、旧梳妆台等杂物,梳妆台上整齐地码着十来本书。
“也不算茶室,就是给我客栈(他的客栈就是边上的老营房改造的)的客人提供一个公共空间,可以一起聊聊天。”“晾竿”解释。
他烧开水,翻出一堆薯片、袋装花生和瓜子之类的零食,乱七八糟地拆开摊了一桌子,再一人一杯速溶咖啡。
我们像穷极无聊的青春期小混混那样坐着喝咖啡,剥瓜子,不停地轮流散烟。他们很自然地就讲起小时候的事,三个人抢着回忆在庙子湖上初中时的糗事。在回忆时,他们再一次掀翻老师的办公桌,在寝室里聚堆赌牌,像所有混小子都干过的那样气哭年轻女老师,偷岛民的鸡和它们的蛋……他们略带伤感地回忆起他们的饭盒——永远的咸菜和咸鱼,没有蔬菜,没有水果。一周回一趟没有初中的东福山的家,反复的咸菜和咸鱼。
要走出去。他们说。都渴望走出去。窒息的人渴望空气那样,渴望走出去。
回忆越走越远,他们说起他们的祖先,那些从温州偏僻山村大胆出走的村民,一百多年前的他们驾着小船来到东海,来到荒芜的快被鱼儿淹没的东福山。
“捞不完的鱼啊!”他们中的一个替百年前的祖先再次发出惊叹,“还有没有主人的岛。”
于是拖家带口来了,温州人,和目前已大部分搬迁至普陀山的台州人。他们的祖先,辟出一条赖以谋生的海路,用岛上现成的巨石,一锤一锤,凿成方块,相互帮衬着,垒成石屋。“没有水泥,石块与石块之间,你难以想象的严丝密缝。”
“就像大理石与大理石?”
他们不答,但是都笑了。
“晾竿”其人我们坐在茶室外的空地上喝茶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晾竿”已经陪我走完了大半个东福山,福如东海、白云宫和象鼻峰。他帮我拍了几张“到此一游”的照片,翻山的时候帮我背沉重摄影包。
浓雾。散了又聚。
另外两个吃完中饭就打牌去了,只剩下“晾竿”和我。
我问“晾竿”为什么不去打牌打麻将。他说现金带得不多,东福山没有自动取款机。
茶室里放着音乐,我们一人躺一把快要瘫痪了的躺椅。这里是海拔米的山腰,空地外是悬崖,悬崖下是海。
我说应该种点花花草草,收拾成院子的模样,夏天的晚上客人在院子仰望星空,感觉会很好。
“晾竿”回答说他有一百多个念头,但总是懒得动手。
清明节前,他雇的两个阿姨会从家里过来,东福山也将进入旅游季。“我连钱都懒得收,你知道为什么吗?”他问完马上说出答案,“因为我总是少收,把零头抹掉。”
“我也不喜欢有太多客人,不喜欢把宾馆扎堆开在一起。”他自顾自地说,“不喜欢烦。我已经不算渔民了,在外面经商多年,但还是成不了纯粹的商人。”
“到我这种年纪,心已经很平了。”他告诉我他四十五岁,“钱多钱少不重要,在东福山,只要稍微勤快点,都不会饿死。开心点,轻松点就好。四十五岁了啊!马上五十岁了,多可怕?还有什么值得计较?但是我为什么也有白发了呢?也没烦心事啊。不不,不是遗传,我家没人有白发。”
他忽然想起问我的职业。我说我是无业游民。他笑笑说不像,就不再追问。
“我猜你不喜欢跟人结伴。”他又说。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我们一起笑起来。
“淡季的时候这里只能呆三天,到处没人,三天后就想逃回沈家门。沈家门也只能呆三天,虽说人多,热闹,但能干什么呢?夜场不喜欢去了,没意思,该玩的都玩过。没几天又想着上岛来。”他接着说他自己,淡淡语气,略带消极的神态都像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的主人公,“我喜欢阴天,或者下雨。这样可以心安理得地呆着。太阳一出来我就坐不住,觉得应该做点事情。昨天晚上我一口气把客栈里所有的被子被套和床单都换了,开始做一件事了,我就停不下来。”
“我知道你为什么长白发了。“
“为什么?“
“因为你有强迫症。”
“对!强迫症!“
我们又大笑起来。
“如果天气好,这里看夕阳很美。“他说。
我说我会再来。看夕阳。看星空。
他执意用皮卡车送我回宾馆,下车的时候我问他还来不来吃晚饭。
“不来了。”他说,在车窗里很好看地微笑,“这个岛上每户人家,我都可以随便窜进去蹭饭。”
道谢,说再见。看着他倒车、开走,我才想起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晾竿“,只是一个不具象形意义的发音。他没那么高,也没那么瘦。当然,他也不胖。
时间:年3月17日周二
气象:阴霾
告别早上起来,东福山变成了雾岛。近海的礁石都灯塔都消失了,山头也整个消失了。
房东说今天再不开,明天就要起风了,那你还得关两天。“小岛就是这点不好。有点事情叫都叫不应。”她幽怨地说,“你看那些人都呆不住了,急着回去。“
从院子里往下看,防波提旁果然聚集着六、七个人。
挨到八点,询问沈家门半升洞发往东极的航班情况,被告知暂时停航。
九点,雾完全散去,再询问航班,尖细的女声果断地说:“停航。“
难以置信!岛居生活残酷的一面这才真实浮现。
“他们(半升洞码头工作人员)看前天来的人少嘛!开航还不够柴油钱。如果像旺季时有几百个人在,九级风都过来了。“房东老板娘忿忿不平地说,”这点雾,对渔民来说根本不算雾。“
就在我心灰意冷准备去拍照的时候,沈家门方向传来消息说十点钟开船。于是飞快地收拾行李,告别房东,去码头候着。
往返三天两夜。第一天上岛,独自兜了半圈,走马观花。第二天,托停航的福,认识了几个人,听了许多故事,才得以慢慢走进东福山。或许,这是一场有预谋的雾。
“东福轮“在清澈的海面终于出现,心情雀跃。刚刚认识的那些人,忽然就模糊了,他们化成东福山细腻的背景或是海平面上遥远的风景。
启航的时候,我在朋友圈上发出一条信息:……完美的旅途,需要出现那么一些特殊的人,丰满你的异地体验,使风土人情更为立体。再见,东福山。
这条信息,那些出现过的“特殊的人“当然不会看到。看到的,是另外一群看风景的人。因为每段旅程,几乎都由一句透着冷漠的台词来划上句号:再见。
再见,东福山。
(完)
原创文字,欢迎转发,谢绝转载
光阴日记北京治疗白癜风最好的皮肤医院北京白癜风治疗最好的医院是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