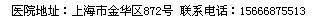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舌系带短缩 > 相关医院 > 岳阳作家手记刘亚卡龟嗲嗲
岳阳作家手记刘亚卡龟嗲嗲
刘亚卡:龟嗲嗲
小时候,我总和嗲嗲(爷爷)(diadia)形影不离。白天伏在他的背上吮吸手指头,口水流湿了嗲嗲的衣背,我可以数得清根根排肋骨。玩累了,就趴下睡觉。嗲嗲的背俨然是我天然的摇篮。醒来,爬上嗲嗲的颈背,便攀上登天的楼梯,伸手数星星、摸月亮。月亮随晚风悄悄躲藏到云里,摸到的只有月光,只有误撞入手心的萤火虫。不知是嗲嗲年纪大了,还是日渐长高变重的我的功劳,总之,他的背驼了下去,像弯弯的月亮,我可以更舒服地倚靠在上面了。
也许是我太淘气吧,嗲嗲的双手得不停从身体两侧伸出来,抓扶我。嗲嗲总被我摇晃得身子左右攲斜,背也就弓成斗笠的形状了。“幺丫头(同辈中排行最小的女孩),你听故事啵?”
“不听不听。”我抖动了几下,三寸厚的脚锥在嗲嗲的手板心里,笔挺了身子,“你讲的故事,不是牛郎织女就是大禹治水······”
嗲嗲并不恼,手在光秃秃的脑袋上来回摸几下,说:“猜梅子(猜谜语),你会吗?”短暂的安静是我最好的回答。
“听好咯------!”不用看,我也知道,嗲嗲此时正抿着只剩牙床的嘴,“能在水里游,能在地上走,背上一口锅,遇险就缩头。”
当时不知道这个词儿说得押韵,只觉得真顺口,一溜就出来了。词儿究竟打是什么“梅子”呢?我在心里反复琢磨着。我得想出来,可不能让爷爷小瞧了我!安静下来的我,在所能知道的小世界里,翻箱倒柜般的搜寻。
“乌------龟------”好一阵时间过去了,我激动地叫出来,比凯旋归来的英雄还神气几分。我缠着嗲嗲还打几个“梅子”,他只嘿嘿的笑,说:“今天没有了。”
我正在兴头,哪里就肯放过他呢。
不打“梅子”了,被浇了凉水的我只好像往常一样把嗲嗲当做玩具了。今天他穿的仍旧是深褐色粗布褂子,就像是乌龟壳的颜色。头光秃秃的,不时向后仰一仰。双手不时伸出来,弯弯的背……
突然发现,嗲嗲好像一只龟,一只还驮着孙女的龟。这个惊天发现让我按捺不住。“嗲嗲好像一只龟!”我大声嚷嚷起来,“嗲嗲是一只龟,嗲嗲是一只乌龟,龟嗲嗲……”
沉默了好一阵子的嗲嗲,嘿嘿笑着说:“龟嗲嗲就龟嗲嗲,你还是个龟幺丫头呢。”他捋了捋长过一寸的几根银白的眉毛,自言自语,“龟嗲嗲还长寿呢。”
成年后我才知道“龟嗲嗲”是不敬重人的话,也就理解了当年嗲嗲的那一阵沉默。
嗲嗲和龟一样吃得也很少。那时,他在四个儿子家吃饭,一月一轮换。妈妈总把一年难得吃上几回的鱼肉,放在嗲嗲来时做。所以每每嗲嗲轮到我家来,我们都像过年一般欢天喜地,盼着久违的鱼肉能早早地端上桌。终于在某天晚上,它出现了,哪怕只有一样菜是期盼已久的,且这碗菜放在中间,被其他菜包围得严严实实的。我们眼巴巴地望着那个大碗。碗里水很多很深,上面还飘着好几片青菜叶,将我们渴慕的肉汤遮住,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我们心急如焚地等着嗲嗲先舀上一瓢。只见他舀了满满一瓢,干枯的手抖动了几下,汤洒落多半瓢。他喝下去时微微皱皱眉头,舌头再围绕着嘴唇舔过去,扯了几下嘴角,望着桌边的三个小屁孩,一字一顿地说:“有---蛮—咸!”我们瞟了妈妈几眼,很担心嗲嗲责怪妈妈。“我不喝汤了!你们要用汤泡饭吃!”我们三下五除二,便把一大碗汤舀得要见底了。尝尝,咦,不咸呀,味道正美着呢!嗲嗲呢,他的筷子不是往坛子酸菜去,就是往每餐必有的冬瓜去,夹几筷子,一碗饭便扒完了。可能是看到我们一脸疑惑吧,嗲嗲边起身往外慢慢走,边抹嘴巴:“汤里多了六坨肉,自然你们吃就不再咸了。”听了这话,我们更糊涂了。嗲嗲又慢慢走回来,抵着哥哥的脑袋说:“六只眼睛掉到汤里了。”想想自己的馋相,脸红的我们才恍然大悟。
上小学后,沉浸在同学为我打开的天窗里。好长时间不和嗲嗲耳鬓厮磨,他的背也不见稍稍直一些,看起来就是一张满弓,我也渐渐忘却了给他取的特有的名号。
我不再有兴致喊龟嗲嗲了。在那些打开的小天窗里,我们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去黄瓜架下,摘下一条,另一头还挂着小黄花。嫩绿的瓜皮上滴滴晶莹的水珠,用手指头从蒂到花一抹,看水成股地淌下来,美其名曰“洗黄瓜”,随后清脆一声,嚼起嫩生生的黄瓜。几个小家伙蹲在黄瓜架番茄架下------这种儿时的水果,一同淋浴着雨水,期待自己长得像它们一样惹人喜爱。
晴好的日子,田野里,山头上,篱坡边,河滩外,一群小屁孩,像巡逻的虾兵小将,无拘无束地游走搜寻。所过之处,只要遇上一丁点儿可入口的东西,哪怕是遍地荆棘,小伙伴也敢于铤而走险。火红火红的覆盆子酸甜酸甜的,绿盈盈的豌豆又嫩又翠,比红玛瑙还美的山梅果能看见都大饱眼福,连蚂蚁嘴里的桑葚也夺过来就吃……
这些时光,让骄阳的炎热都淡去了不少。知了肆无忌惮的歌唱,它们给大人催眠。在小孩这里,那是热情洋溢的号角。趁大人打瞌睡,我们溜出门,毫不矜持地接受知了的邀请,满怀激动地加入到它们的演唱会。
离开学只剩一二十天了,好玩的,好吃的,在漫长暑假的前一半时间里一一疯狂地尝试过。爬满嘴角的贪婪,被一种新长出来的东西取代。
起先它让人毫无察觉,等它不忍忽视,用痛来提醒你的时候,它的尖尖已长得像桃子又绯红又小巧的嘴巴了。这是妈妈形容的,似乎它美得赛过樱桃。它的长势多喜人啊。四肢自然是它常常光顾的场所。宽敞的地方似乎也太惹人注目了。顽皮的它们选择了在眼睑里面,眼皮眨呀眨地难受;胳肢窝前后两侧,因它们的神奇出没,胳膊不再灵活转动。特别是头上的,起初躲在黑发中,多了一层天然屏障。不要几天,它的茂密程度赛过了雨后春笋。大人们等这些身体的入侵者长到成熟了,它的尖尖会像小鸭的嘴蛋黄色了,弄破它,再将里面的脓水挤出来,才算控制住它。
这比牛魔王还牛魔王的形象,让我好几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野孩子的本性并未收敛。别的地方去不得,到嗲嗲那里玩玩总是可以的吧。
嗲嗲住在大伯家的小厢房里。“小厢房”这么美好的名字,曾让黄毛丫头的我以为是“小香房”-------小巧玲珑,还散发淡淡香味。走进那个低矮的屋子,一张刚靠近还没来得及坐上去,就咯吱咯吱荡起秋千的床,已飘下粒粒灰尘和片片枯叶。屋顶上一块小字本大小的亮瓦,是这间小厢房的顶灯,也是这房子的追光。灿烂的日子,透过亮光,我伸手可以摸到那束追光下舞蹈着的灰尘精灵。嗲嗲常戴了老花镜,坐在那束光下,一手将书按在膝盖上,一手拿扩大镜,看着发了黄的皱巴巴的书。
眼前的这些景象,让公主“小香房”的幻想支离破碎。它不过就是正房旁搭建的一间小屋子,连屋顶的高度也没法和正房相比。人口少的人家,这间屋子里养着猪,喂着牛,关着鸡,睡着狗,上面写着“六畜兴旺”的字样。取这么儒雅的名字,大概是因为喊“偏房”或“门垛子”有点羞于出口吧。
我的兴致只在小厢房里唯一的家具--------一张两面靠墙的长方形桌子上。不大的桌面上,堆满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盒子。装白糖的瓶子是个鼓肚子形状;盛南瓜子的是生了锈的铁皮罐;皮蛋坛子,放在最里边。手伸进去,摸到蛋,凉凉的。皮蛋是姑妈不知在过哪个节时送来的,有时摸出来,蛋壳上有虫子蠕动,也影响不了我们的食欲。敢跟我抢东西吃,没门!不管那些,用嘴吹走或用手拉掉了,照样心满意足地吃下皮蛋。几颗老冰糖放在白色的瓷碗里,有一个小巧的盖子盖住。只要一咳嗽,嗲嗲就会拿出一块放到我们嘴里。所以,每次会习惯性咳嗽,为了得到那满口的清甜。有时假像真做,吃得太馋,呛住了,真会止不住的咳嗽。嗲嗲端来茶,嗔怪着夜里得盖住肚子啦。我们就很配合地点头。
今天,嗲嗲这里,会有什么来塞馋猫的牙缝呢?
还是和原来一样,在艳阳高照的午后,嗲嗲坐在那束追光下,老花镜已经架在了鼻尖上。但他身后围了十来个人,我钻过人群,瞧见嗲嗲左手抓住一个男孩子的螺丝拐(脚踝),右手握着毛笔在螺丝拐上轻笔细描。那握在手心的毛笔已经竖在手的虎口了。放在平常我们这么拿铅笔的话,嗲嗲肯定会小题大做,抽走笔,摆出生气的嘴脸,教导我们:笔得向后斜一点!今天让我逮到嗲嗲这握笔的模样,少不得多给几颗老冰糖我才罢休。正要张口数落嗲嗲,在昏暗的小厢房里,我清楚地看到,那些光着脚,泥巴沾满裤腿的大人,个个都摒住呼吸,定定地瞅着嗲嗲的右手,生怕稍不留神,就会错过什么似的,神色膨胀成我不曾见过的庄重,我只好把那南瓜子的香、老冰糖的甜,和了口水,用力往肚子里吞。嗲嗲耸着肩膀,伸长了脖子,弯着腰的模样,让“龟嗲嗲”的名号没由来地涌入我脑海。龟嗲嗲嘴里肯定叨念着什么,他的嘴一张一翕的,只是没有发出声音。我凑近了想要听清,也是徒劳。那样子有点像唐僧念紧箍咒。可我不知道会不会像猴哥那样,念得“螺丝拐”疼痛难忍。
“螺丝拐”呢?
红里透黑的脸,一看,就想到酒桌上的扣肉皮。一件绿了吧唧的背心,露出厚实的膀子。咦,这不是好出名的狗儿吗?(乡下人喜欢给男孩子取小名,小名越贱,孩子就越能健康长大。)他的学名不知是啥。但进了学校门的,没有不认识狗儿的。我们学校只有三栋土砖教室,呈撮箕形分布。所以事无大小,全校皆知。狗儿常常因为迟到、打架、骂人,或没背课文、没交作业站在教室门外。夏天,狗儿在一边凉快;冬天,狗儿在风里发抖。
虽然我确信这个人就是狗儿,可眼前的狗儿又多少让我感到一点不太真切。因为我只见过他“飞天蜈蚣”的淘气,从未见过他的安静,现在都有点俯首贴耳的模样了。想必嗲嗲的叨念,有紧箍咒的威力吧。否则怎能制服住飞天蜈蚣呢?
嗲嗲的笔点染勾画多久,就叨念多久。等狗儿站起来,一只小巧的乌龟黑黑地停驻在他的螺丝拐上。嗲嗲撕下一块鸡蛋大小的黄牛皮纸,稳稳当当地贴在“乌龟”上,严严实实的将它盖住,他捋了捋下巴的几根胡须:“明天这个时候应该不痛了,后天这个时候就好了。”
嗲嗲简单的几个字,这一屋子只会对弯腰的稻穗、饱满的玉米、剽悍的黄牛另眼相看的人,此时的瞳孔,变得豁亮豁亮的。
只有我,充满疑惑。嗲嗲是什么时候会画龟的,叨念的究竟是什么,龟和身上的疮疱有联系吗……
此后,我常常光顾嗲嗲的小厢房。听到那些人个个都喊着我的“龟嗲嗲”,他们龟嗲嗲长,龟嗲嗲短,龟嗲嗲前,龟嗲嗲后的,起初我心里蛮郁闷的。但大人小孩的那股子亲切,龟嗲嗲自己笑着,皱纹像一朵菊花似的铺开,乐呵呵地拖长了声音应答“哎-------”。我只好大度地接受专属于我的宝贝被充公的事实。
龟嗲嗲画龟治疮疱的佳话在乡里乡亲传开了。从落英缤纷的春末到植物孕育果实的盛夏,再到月圆中秋,龟嗲嗲不知画了多少只龟,治了多少个疮疱,贴完了多少张大黄牛皮纸。如果说龟嗲嗲的背,以前像背着口平底锅。现在,画完这一年的龟,平底锅都换成一个老南瓜了。
在缺医少药的年代,龟嗲嗲的“龟”,无异于每一株植物都享受得起的及时雨。“龟”由孩子的身上,画到了大人身上,老人身上。消化着红米饭南瓜汤的乡邻,端来了豆腐脑,送来了兰花豌豆,包来了红糖,那句打心眼里的“多谢打”,让龟嗲嗲脸上菊开不败。
冲画龟的悠闲,冲隔壁左右对龟嗲嗲的敬重,其实最冲人家送来的各种吃货,可我不能说出口,总之我无比神往起画龟的方法来。我天天站在龟嗲嗲身旁看。趁他去二伯三伯家和我家吃饭,饭前还少不得帮他们做事的时间里,我偷偷拿了毛笔,照着龟嗲嗲的招式画了好多只乌龟。尽管不知道具体内容,我也有模有样地叨念着。连做梦都是我在帮哥哥画龟,总是凶巴巴的哥哥,在梦里,在画龟时,他温驯得像羊羔咩咩。
在学校,或大或小的学生,渐渐知道我是龟孙女了,羡慕的眼神,让我的背挺得笔直笔直的。龟,我的确已经画得熟练了。闭上眼睛,都能画得有模有样。有几次,我故意要爷爷督促我写作业,请他坐在板凳的一边,看着板凳另一边的龟孙女。窄窄的板凳上,我将偷来的毛笔拿出来,爷爷的眯缝眼睁得圆溜溜的,我三下两下,画出几只龟,递给爷爷,期许他点着头捋捋胡须露出笑容。然后把我拉到腿上坐下,对着我的耳朵,说出神秘的口诀。这情景,想一想,让我激动得好多次感觉到心要飞出来。可每次,爷爷缓和了脸后,只拿眼睛扫我,从头发丝到脚丫子,一遍一遍地扫,好像这样可以把我打扫得一尘不染,出落成神仙姐姐似的。
龟,爷爷画得越发多了,都不知道画过了几多春秋。爷爷的背也越发地驼了。
秋收过后,棉花也庸懒起来,有一朵没一朵的,挂在枝头。清闲了的庄稼人,把儿亲女嫁的大事,在秋高气爽的闲适里张罗开了。丰收的欣慰和婚嫁的喜庆,在这饱满的季节里,像是双胞胎比高矮!
一天清早,从屋场西头传来嘈杂的声音。我们站在屋场东头,也能准确地判断声音源于大伯家。几近无奈的哀求,隐约飘来。还有压抑着的女人的哭声。我们急切地想弄个明白。可妈妈从不允许我们去看,说是孩子别趟浑水。
放学回家,谜团还是那个谜团。爸妈那天似乎比平日忙一百倍,我们肚子实在饿了,煤油灯的芯拨了三次,他们仍没回来。除了肚子饿,还有隐秘的原因。在那些只有鸡屎鸭食猪菜相伴的日子,我们的好奇心疯长得青面獠牙。
到底是大伯家还是小厢房有事?尽管连这都还不清楚,但我们依然隐隐有些不祥的预感。
直到第二天上学,才从同学口中得知龟嗲嗲的晚节不保的事实。听到“晚节不保”几个字,我的震惊不亚于置身火山喷发口。
原来,那个隔了三道田坡的英子,被外出打工的男朋友,无情抛弃了。狡黠的男孩,只说记起英子曾脸上、头上几只黑乌龟的模样,就做恶梦。可怜的英子,昨天哭到龟嗲嗲这里,无力地哭诉:当年怎么就给她画了那么难看的龟?
从此,“龟嗲嗲”彻头彻尾地消失了,连同他的毛笔、黄牛皮纸,也连同香脆的兰花豌豆,连同一声笑容可掬的“多谢打”。
其实,爷爷年事已高,背驼得不成样了,不画龟了,作为子孙,我们巴不得呢。可爷爷的“晚节不保”,又让我们惋惜、心疼。
我尤其不甘心!那几句口诀我还全然不知呢!白白把龟画得那么熟练传神了!现在我已经彻底失去了掌握“画龟”精髓的机会。在爷爷面前,连“龟”一类的字音都不能提了,哎。
口诀,大概陪着爷爷一起在黄土里沉睡了吧。外出求学的快乐与艰辛,让念念不忘追寻的“口诀”渐渐遗忘。偶尔想起,还是惋惜不已。如果没有晚节不保的事件,爷爷会把“口诀”传给我吗?不会真有传男不传女的说法吧?
对爷爷的不传,我只能一笑而过,只是感到惋惜!曾悲催又豪迈地想:有多少散落民间的“画龟”,被日渐发达的现代文明,甩到岁月的末端,日晒雨淋,风化成粉末,直到淡出人们的视线,似乎不曾出现过!!!我不能想这些。因为想到这里,总感觉,那被粉碎了的,还有我的心。
······
八岁的儿子,暑假眼睛不适。医生检查说,结膜炎。吃药打针数天不见症状缓解,反倒越发红肿了。外公心痛外孙,要接到他家里,说采撷露水洗洗吧。露水是指望不上的,但老爸的心意不忍推迟,反正也不会有副作用,就答应了。
三哥看了,说是严重的红眼病毒。迷信的二伯说是犯了土煞。五嫂担心的说,不会是肿瘤吧。大嫂看了又看,用左手的食指和大拇指,顶开儿子的上下眼睑,翻开里面的血红的肉,上看下看,再收回手,松了一口气,说:“是‘挑疔子’嘞。”她进房间神秘地拿出墨汁毛笔,还有久违的黄牛皮纸。我仿佛一下子回到儿时,龟嗲嗲手握毛笔,嘴巴不由自主地叨念起来的情景。两天后,儿子眼疾痊愈。
这么多年,我不知道爷爷把我迫不及待想得到的“口诀”,竟然传给了大嫂,这个刘家的媳妇。它传承了下来,它现在治好了儿子眼睛上的“挑疔子”,无论大而言之,还是小而言之,我都没有理由不深感庆幸。但我偏偏对爷爷的选择,难以释怀。我反反复复打量着大嫂,希望找到她的过人之处。这个相处了二十几年的人,如今已当上了奶奶,仍是一身土得掉渣,仍是一脸的慈善菩萨相,仍是胆小得连一只蚂蚁也不敢踩死。在大哥剖鱼时,仍是闭上眼睛念:鱼儿鱼儿你莫怪,你本是桌上的一碗菜。除此之外,我还真没有新发现。
何以得到爷爷的真传,我曾问大嫂,她只是笑而不答。弄得我一时对大嫂羡慕嫉妒恨。爷爷的“画龟”和传大嫂的原因,都成了谜。我一度因解不开谜而迷惑,迷惘。
四十岁生日那天,爸爸把我拉到一边,揭开了困扰我多年谜团的神秘面纱。
原来“画龟”不仅在于口诀,更在于画龟人不可滥杀无辜,得心地善良。否则,就不再灵验。
这个原因太简单了,好像冥思苦想的难题,最后用来解答的途径不过是:1+1=2。简单得我一时回不过神来,却需要用一辈子反思。选择在我四十岁时告诉我,也是爷爷安排的吗?四十而不惑。爷爷是希望我能遇事不惑,更期待我以后不惑,明白做人吗?!
“龟嗲嗲,龟嗲嗲······”我在心里深情的呼唤,驼着老南瓜的背,重新变得清晰,我只有由衷的敬畏!
作者简介:
刘亚卡,岳阳华容实验中学骨干教师,爱好写作,文章常见在各报刊杂志及网络。
相关阅读:
刘亚卡:婚礼中的父亲
赞赏
人赞赏
北京治疗白癜风价钱治疗白癜风的口服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