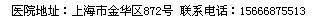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舌系带短缩 > 饮食调养 > ldquo世道兵荒马乱,有你的地方
ldquo世道兵荒马乱,有你的地方
北京哪里有专治白癜风医院 http://pf.39.net/bdfyy/bjzkbdfyy/index.html
欢迎你打开九号酒馆的第篇故事
“小二,上茶”
01
大暑,黄河关酷热难耐。打边陲一路逃荒至此的人们怨声载道,最后半分理智被辘辘而来的马车扰溃。
车夫鞭笞马儿抢占人道,元七同难民一起被迫退开。她抬眼去看马车,陆闻安恰巧掀帘探出头来。一人脂粉清淡,一人满面枯黄,却都没将对方看进心里,转瞬便错开视线。
人与马,你说我嘶许久,终于偃旗息鼓分散在河边歇息。
正值李子成熟之季,郊野的树上结得茂盛。元七将母亲安置在临河的山丘下,朝陆家马车停靠之处走去。
陆老爷原是位京官,如今惹怒圣上被贬,家中骄奢惯了的柳小娘悲从中来,闹得一家人鸡飞狗跳,直到现在仍哭天抢地。
陆闻安无甚反应,倒是陆老爷被烦得掀帘下车。柳小娘抹泪追出去,却嫌石头路咯脚,转而扶着山壁拿头去撞。
山丘上有几株果树,元七提裙飞身而上,这人偏生蹿出来,好在她蹬了脚石壁才没踩着她。柳小娘颅顶一凉,哭得更是泪水汹汹。
陆闻安道:“姑娘不必理会作死之人。”话里全是讽意,却正合元七的意。
柳小娘气得叉腰,方至马旁帘子被陆闻安重重放下。她仰头靠到车窗上,元七垂头这白皙的脸恰巧撞进眼眸,虫蝇作祟,她伸手赶时手中李子滑出去。
只见那李子“咚”砸到车顶,陆闻安睁眼。四目相对,元七心生窘迫,好在眼神飘忽之际瞧见河边的母亲要起身,遂拔声喊:“娘。”
是时,蹲在河边掬水的陆老爷也唤:“闻安。”陆闻安应声:“哎。”
她发誓应完之后才意识到辈分拔高了,可树上的降辈之人已铁青着脸唤:“我这便回去,您别过来。”
在河边偷得几分凉爽,陆家父女俩不愿回去听柳小娘唱戏,想寻个坐处却被难民排挤。
元七手边有块能容三四人的石头,陆闻安走过去时一身形魁梧的汉子往上一坐,腿横其上。元七睨眼陆闻安,朝汉子扔去几个李子。“挪挪位置。”
汉子卖她面子,干脆另寻他处。陆闻安搀着陆老爷坐下,低声道:“多谢。”
“莫谢,”元七提唇讥笑,“大暑的日子他是怕与富贵之人坐在一起长痱子。”
陆闻安也不恼,心想:还当你不会笑呢。
02
落难的凤凰不如鸡,陆老爷被贬黄河关通判,月银一落千丈,留不住水做的柳小娘了。
这晚月黑风高,柳小娘背着细软悄然出逃。她到了郊外河边却没看见接应的马车,急得酝泪。不急不遑跟了一路,陆闻安唤她一声后走出漆黑。
陆闻安,生性凉薄,克死生母却不见其伤心分毫,京城名门与官户争相轻侮唾弃之人。以前偌大的陆家柳小娘便独惧她一人,如今大宅变斗室,这份惧怕更甚。
但见她两股战战,边退后边哭嚷:“我是投错了胎入了你陆家的门,被你父女二人这般糟蹋作践。你发发慈悲放过我罢,我求你了。”
陆闻安轻睨她肩上包袱,“把你偷的银钱交出来。”
柳小娘含泪躲避,只须臾便被逼下河,脚底打滑栽入河中。登时水花四溅,几米外正提灯捉鱼的元七吓掉了灯。烛火将宣纸烧燃映亮水面,柳小娘寻亮看去,瞧见元七双腿,手一松险些滑回水中。
元七见此走到栈桥边坐下并抬起双脚,怕落魄大户家的小娘子喝着自己的洗脚水。陆闻安被她逗乐,没忍住轻笑出声。元七正欲看她,灯笼忽然熄灭,周遭陷入漆黑。
瞧不见有趣之人,陆闻安面色恢复如常,走到柳小娘身侧劫走包袱:“你非要逼死我吗?”柳小娘攥住她衣裳声泪俱下。
陆闻安不为所动,找到银钱方还回包袱。柳小娘仍不愿撒手,她便抚上其腕上玉镯,柳小娘立时攥着手逃开。
待她恶鬼追赶一般跑没影,陆闻安边拧衣裳边往岸上走。栈桥上发出声响,她闻声回头借月光瞧见元七身影。元七也瞧见了她,叹出口气拎着鱼篓朝她走去。
逃到黄河关的难民有的选择去往都城,有的则选择留下,被知县安置在废弃的巷子里。快到巷口,元七给自己揽下的护送差事了结,抬脚便要回去。陆闻安出声:“我叫陆闻安。”
元七滞愣一瞬后回首道:“冬月初七所生,元七。”
元七家住在巷头,她母亲受病痛折磨夜间难眠,此刻听见说话声遂起身点灯。
光透过草棚缝隙将眼前渲染得敞亮,陆闻安总算看清了元七的脸。许是安定后将养得好些的缘故,她皮肤白皙许多,将清秀的五官衬得更加打眼。偏生这明媚的眉眼间含着几分戾气,容易叫人避而远之。
听见元七母亲唤她,陆闻安便同她道别。
本无心管她,奈何瞥及她裙摆浸水,元七从身后竹竿上扯下件衣裳追上她。衣裳与鱼篓在同一只手上,元七塞给她衣裳时被她勾住鱼篓线。
元七走了两步被扯回去,陆闻安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她便从鱼篓里捞出条鱼用衣摆紧紧包住,随后塞给她鱼篓扭身跑走。
这……看着同鱼缠斗且忙于应和母亲呼喊的元七,陆闻安扶墙发笑。她错了,那眉眼间的哪是戾气,分明是憨气。
03
翌日清早,街边客栈的门被打开。黑衣束发的元七跳过门槛进去,再出来手里端了条长板凳,往门边一搁便大爷状坐上去。
世道乱,往来者打尖住店全靠这一间客栈,掌柜的胆小要寻人看店,遂让元七捡了这份差事。
不等她坐热板凳,几个佩刀的衙役从客栈前匆匆走过。河边惊现女尸,经证实乃陆家柳小娘。更夫道昨夜目睹陆小姐尾随柳小娘,眼下衙役正在去陆家抓人呢。
无多时,陆闻安被几名衙役带往衙门,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百姓。
陆闻安面色平静,瞧见客栈前的元七时却目光乍明,唇畔微扬。险些溺于这张冷清的脸上一闪而过的温柔,元七回神混入看客之中。
黄河关通判一职向来空缺,知县一人独大惯了。如今凭空多出位通判,府衙上下谁也不舒心,眼下柳小娘横死郊野,正是打压陆家的时候。
陆闻安方踏入公堂,衙役扬起杀威棒欲打她腘窝叫她跪下。元七心一惊正欲拨开人群上去,她却往前一步从容跪下叫杀威棒扑空。
漠视知县脸色,陆闻安说得不卑不亢:“昨夜柳小娘欲离开陆家逃出黄河关,因她偷窃民女家中银钱民女才一路追到河边,讨回银钱后便没再追她,不知她因何而死。”
一番话听得看客们又笑又惊,知县却光捡想听的听,扬袖道:“没有证人凭你一面之词不能脱罪,收押候审。”
他方说完衙役便上前押人,陆闻安寒下脸反手将其甩开后起身:“民女并未犯罪何来脱罪一说?大人若是想借此事打压民女父亲大可不必,若民女当真有罪他定会将民女亲自送到府衙,不会劳烦大人。”
“大人说收押便收押,多舌狡辩做什么!”衙役被她推开心中不爽,收到知县眼色便用力推搡她。
她未防备,踉跄之后扑摔到地上。堂下百姓见怪不怪,唯独元七见衙役要抓陆闻安衣领冲了进去。她身手敏捷其他衙役尚未反应,她已踢开伸向陆闻安的手俯身将人揽起来。
两人方站稳,知县高喝:“大胆!”余下数名衙役立时一拥而上。
元七将陆闻安推开,捱了一闷棍后跌到堂案前,几个衙役持着杀威棒将她围住。他们扬棍之际,堂下一穿着破烂麻衣的女娃高声哭喊:“别打阿七姐姐,是打更的哥哥抢手镯把人害死的,我都看见了。”
众人齐齐看向女娃,知县与衙役大为愕然。吃到几嘴灰的元七轻咳出声,陆闻安忙去搀她。
知县传喝更夫,更夫道昨日自己抱病,弃巷难民里一男子代了自己的职。不足两刻钟,衙役便将逃至郊野的犯人追回。不待知县严词相骇,担惊忍怕整夜的犯人便从实招来。
柳小娘染血的玉镯被呈上堂案,陆闻安与知县一同看向玉镯。两人目光交锋,她扫眼仍厉色盯着元七的衙役,伸手将镯子推给知县。“这是当初承露台建成时圣上赏赐家父的,求大人行个方便。”
避开堂下百姓将玉镯掩进袖中,知县松口:“走罢。”
“陆……”元七方蹙眉,陆闻安搀着她离开,低声道:“给你一个殴打官差的罪名,你娘谁来管?”
同陆闻安一齐跨出衙门,元七没来得及看她两人便被出来的看客挤散。
“穷山恶水出刁民,压根不该让他们留下,造自己的孽害别人的命,竟还要倒打一耙!”闲言碎语里这些话直钻进耳朵,元七缩回寻找的步子,避开人群捂着腰忍痛快步离开。
几声呼喊钻进耳里,元七扶墙停下,回头看见小跑而来的陆闻安。
“元七,”见她回头陆闻安碾笑道,“他人功过与你无关,你是你。”
熏风刮眼,元七趁着揉眼在袖下释笑。
04
“砰!”鱼篓砸到屋顶和茅草一起掉到身上,灰尘四起。元七呛得咳嗽,虚睁着眼从两张长条凳上坐起。耳边是咒骂和赶他们走的声音,她叹出口冗长的气,阖眼时仿佛被拉回十年前哭声参天的大宅外。
“承露台……建成。”她慢慢吐出这句话,方睁眼屋外突然传来母亲的咳嗽。她连忙跑出去,看见了被镇上百姓推搡的母亲。那人再要动手,她走过去取下挂衣裳的竹竿直指其鼻尖。
“走。”吐出这字的元七目光狠厉,镇上百姓纷纷闭口。不知是谁道:“她是帮客栈看店的打手。”他们才悻悻离开。
补葺完屋顶,元七为母亲熬上清粥后照常去客栈看门。
元七离开不久,陆闻安提着两尾鱼出现在巷口。瞧见脚下一片狼藉,她心口狠狠一闷。
元大娘瞧见她满面疑惑,她提起鱼柔声道:“我是元七的朋友,这是之前她寄养在我那儿的鱼,带过来给您熬汤。”
“啊,进来坐。”元大娘支着膝盖起身,枯瘦病态的面上挤出和蔼的笑来。
鱼汤的香味在简陋的屋子里传开,元大娘一面搅汤一面偏头咳嗽:“我来罢。”陆闻安接过勺子轻轻搅着。元大娘对她一笑,哑声道:“听说小姐是京城人士。”陆闻安颔首。她似乎想到什么遂沉了眼色:“有我拖累,阿七不知何时才能回京。”
“回京?”陆闻安拧眉,元大娘回过神忙摆手道自己胡言乱语。
喝过汤又扶元大娘躺下休息,陆闻安方离开。她还未出巷子,横在巷尾的帘子后面传来女童的哭声。她上前掀开帘子,看见此前作证的女娃正被其他孩童欺负。几个孩子见有人来纷纷跑走,她蹲到女娃面前轻声问:“你叫什么?家在哪儿?爹娘呢?”
“七九,家和爹娘都没了。”七九说得极轻,且瑟缩着往后躲。看见她额上淤青,陆闻安向她伸手:“跟我回家罢,不会饿着你的。”女娃犹豫许久后忍泪握住了她的手。
那厢,元七跑遍镇子,终于用仅剩的钱买到了母亲今明两天的药。她将药塞进衣裳踏入客栈,门边的凳子不见踪影,她疑惑地看向掌柜。
掌柜甩手朝她扔去工钱,她抬手接住后掂了掂,不足半贯。不等她问,掌柜便道:“此前你从店里顺着走的两张板凳和馒头,够抵半贯钱。”
“馒头你是说低价卖我,从工钱里扣,而凳子是你以多余为由所赠。”元七攥住钱提唇讥笑,“我并未偷抢,只是买了几个天价馒头。”
她转身一只脚才悬到门槛上,店里吃酒的客人高声讽道:“攀上陆家小姐又如何,陆家是重建承露台的功臣,与刁民有云泥之别!”
元七感到心凉,重建者功名俱收,她父亲作为初建者却含恨而亡。
顶着烈日颓然行在街上,元七走到泥墙旁时被一大一小的两人挡住。
抬眼,陆闻安同墙后绚烂的紫薇花一起撞入眼眸,扎到心口。陆闻安,是她所悦之人。亦将她看进心底,陆闻安掏出几枚铜板让七九去买糖葫芦。
待七九跑远,她负手气定神闲地凑近元七。近得气息相替,元七惊得退后。她得逞地扬唇,“元七,留下陪我罢。”
退缩之人没藏住眼中瞬间的欣喜,可不等陆闻安欢喜她便狠了眼色。“陆家小姐,你让我以什么身份留下?你给我身份吗?”
语出,陆闻安黯然垂首。对啊,她得意忘形,忘了离经叛道,清议不容之情难入世人双眼。忘了母亲正是因她退婚何家,说心悦女子才气得心疾发作离世的。
预想到这样的沉默,元七咬牙将她绕开。待元七走远,她艰难地追出去几步,喊道:“等我。”
05
镇上百姓与难民的矛盾愈发严重,弃巷里不时被泼进脏水,更莫提恶语相向。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大雨来临,骂者挨骂者皆被困于家中,徒有雨水光顾。倒出药罐里最后一点汤药,元七走近床边将母亲扶起来,凉风吹进来,人猛地咳嗽两下竟然见血。元七用袖子为她擦去嘴角血迹,沉着脸将药喂下。
待雨小些,元七拾起门边斗笠朝药铺走。她到时大夫正同七九讲如何用药,看见她连忙绕回药柜前取药。
她走进去,七九伸手捏住她衣袖,“阿七姐姐,我家小姐病了,你去看看她罢。”
“病了?”元七听得蹙眉,蹲下身正欲问她详情大夫抓完药对她道:“能喝小半月,走之前领你娘来扎几针罢。”他想想终究没说出之后的话——还能多撑些时日。
“好,多谢大夫。”道过谢,元七拉着七九便跑出药铺:“如何病的?严重吗?”
“老爷打她,还罚跪好几日,今晨淋了雨便晕倒了。”七九说得快哭一般。
元七脚下焦急,谁知两人未跑出多远,元七邻户的汉子冒雨跑来,拉起她便急匆匆往回跑:“你娘身子熬不过去,着急见你呢!”
她听完一愣,松开七九拼了命地跑,任七九在雨里跺脚呼喊她全然听不进去了。
元七火急火燎地赶,跑得纳口气都疼,可她赶到时母亲竟在她眼前被醉酒的镇民推倒在地。强压下一瞬间头晕目眩的感觉,元七冲上去推开醉汉,跪到积水里紧紧抱住母亲。
邻户连忙与其他人一起将醉汉赶走。醉汉的骂咧声还在耳边,元七揽着母亲颤声唤:“娘你说话,我回来了你说话啊。”
她泣不成声,唤久了便说不出话,几个人见此情形皆噤声垂首。
不知跪了多久直到两腿发麻,元七终于抱着母亲起身进屋。听不见屋里的动静,邻户轻声问:“那醉汉何时来的?”一妇人登时大哭。“你前脚刚走人便来了,借着酒疯抄家一般。皆不将我们当人看,空长着脑袋胡乱欺人!”
黄河关的雨整整下了几日,似将犯涝灾一般,下得人心慌担心出什么祸事。这不,夜里陆家邻户的牛棚便倒塌了。附近的百姓皆手忙脚乱赶去帮忙,去得急的甚至未披蓑衣。
元七趁乱走近这家人的院子,看着人们又是救牛又是抢修竟然想笑。
牛被压在根柱子下面,堪堪撑住棚子。元七走进人群,抬腿一脚踹在牛脖子上,牛立时冲出棚子,整间牛棚彻底崩塌。
人们怒目瞪她,家主更是挽袖冲了上去,可看清来者脸时却气焰全无。她俯身自废墟里抽出根玉米杆,一鞭一鞭抽在当日的醉汉脸上,抽得人哭天告地。
七九搀着陆闻安到这户人家门口时元七正出来,两人迎面碰上却都无言。陆闻安滞愣片刻后将伞撑到她面前。
即使注意到陆闻安面色煞白元七亦无力多管,她隔开伞要走。陆闻安看见她肩上包袱,急得脱口而出:“你要去哪儿?”她回:“京城。”
“去做什么?”“寻人。”
她已迈出去步子不愿多说,陆闻安分寸全失,“我说过让你等我啊。”
可惜,她喊的人身形诀别。
06
弃巷的难民逐渐去往别处,茅草搭的陋居被隔岸观火许久的官府一夜拆除。
陆闻安仍与守正不移的陆老爷死磕,最后病痛共受,卧床伏过了整个末伏。末伏一去,泥墙后紫薇花谢,叶子发黑萎缩徒留一树垂吊的蛹。
陆闻安昧了神,又恢复往常寡言独居的模样。有的人是人去,有的人是心去。
直至临冬,一封快马稍来的何府婚帖将陆老爷动容。而陆闻安得知是京城所寄,立时喜不自禁,神容俱活。
一路舟车劳顿,赴宴当日陆闻安却未出席,只戴上顶帷帽掩于人后去向已成废墟之地——袁府。
十年前,袁将军休兵回朝,正值新帝即位。新帝崇迷道法妄求长生,遂命袁将军征民修建承露台,欲接食甘露塑不死之身。后承露台倒塌,偏逢圣上大病,与袁将军有隙者诬陷其偷换用料,以至袁家满门抄斩。
门轻轻一推便破开,陆闻安拈散手上沾到的藓灰,踏过掉落的封条进入大院。入眼尽是荒芜,花树枯死,墙木所裂之处攀满藓皮,所谓人亡宅死。
陆闻安伫立良久,被吹得咳嗽方退出废院。
她望向巷口,初见元七的情景浮现。那日天晴,同母亲出去抓药的陆闻安在途径巷口时听见哀哭声。她折回巷口,瞧见一束发女童跑进去,方至门前院内冲出位官兵挥刀便欲杀她。
陆闻安忙跑过去一把抓住女童,喘着气恨道:“臭小七,再乱跑回去让掌事姑姑打你板子。”
官兵与女童俱惊,她仰头对官兵道:“她是我家丫鬟。”恰巧巷口出现一妇人唤:“闻安。”
官兵虚眼见是陆夫人,拦住要出来的差友赶她们走。陆闻安连拖带拉才将元七央出巷子,她再想回去却被陆夫人紧紧捂住耳朵抱走。
她记得,母亲当初将元七托付给了袁将军被流放的部下。
石块磕碰墙壁将陆闻安思绪拉回,她寻声望去,元七停下步伐,看眼两人在地面交叠的影子方抬首。
仍是不经意间逢于意外,涟漪难平。陆闻安瞧着惯常袭黑衣束发的元七,碾笑上前两步。
元七忍住乍然的欢喜,转身跑出几步却又折回,不待陆闻安说话便攥着她的手走到街上。“罪臣旧宅岂能随意地来?”不长不短一句话,让她说得似恼非恼。陆闻安反手钳住她,轻声道:“你在黄河关才记起的我?还是一直记得?”
被问之人深吸口气,似下定了莫大的决心。“从未忘记。”
元七送陆闻安回客栈时,陆老爷与七九恰巧回去,四人在店前碰个正着。
元七垂眼,向陆老爷行礼后欲走却被陆闻安拉住。陆老爷睨眼女儿的手,几经尝试也未松下板正的脸,最后于心底叹气,道:“我与何大人还有事商议,你们先回罢。”
待陆老爷进去,陆闻安与七九皆笑。元七不解地拧眉,她道:“身份已有,愿同我一起回去否?”
元七失语,只定定地凝着她似要将她刻入眼珠。十年,她从未忘记当初救自己的人,也从未忘记构陷父亲的何大人。从前仅有报仇一个念头,如今多了陆闻安她不知该如何抉择。
而于陆闻安,她深知自己并无资格要求元七放下血债和仇恨,问一句“愿意否”已贴尽颜面。终是一人说不出一人不敢说,沉默良久。
起风,陆闻安忽然掩嘴咳嗽起来,元七欲问她却牵起七九离去。
元七呆愣地立在原地,待她双肩塌陷,希冀下沉之际七九却一路小跑而来,跃过门槛径直扑到她身上。“阿七姐,我家小姐挨了许多罚生了许多病,如今已落下病根。老爷都心疼允她来寻你了,你同她回去罢。”
不待元七开口,她又埋头跑回去:“马车明日辰时来接!”
翌日,天色未明,何府后院的门被推开,一奴仆装扮的男子拄着手杖踏过门槛。元七自角落里走出来与之碰面。
她扫过他落疾的腿,歉疚地垂头,未开口他却先道:“阿姐,陆小姐是值得相守之人,你去罢,何家有我盯着。”
当年是她带着他偷溜出府玩耍,途中与他争吵,扔下他负气回家才弄丢他的,此后他又独自藏在何家那么多年,她怎么能轻易自私地离开?
“走罢,必要时我会找你。”见元七不肯走,他退回去将门阖上。反正圣上已经有意调回陆老爷,或许不久后她便能回来,能得知冬月初七何守承惨死家中的消息,能为他这个刺客烧些纸钱。
辰时将尽,客栈前的灯笼熄灭,往来者仍只有小商摊贩。手中的汤婆子已经凉透,陆闻安狠拧眉心,牵起七九走向马车。
“小姐再等等罢。”七九两脚抵地,急出哭腔来。
“等不得,早些赶路才能吃上驿站的热茶。”车夫挑起斗笠冲二人笑道。
七九喜上眉梢,拔腿扑过去。“阿七姐姐!”
顺顺她头发,元七抬头向呆愣之人伸手。陆闻安好半天才回过神,又气又喜却都抵不过心底无尽的感激。
陆闻安将手交至元七手心,两人相视一笑,归家!后记
半月后,朝廷重臣何守承病故,袁将军冤案昭雪的消息传至黄河关。彼时,元七与陆闻安正立在镇口等陆老爷,听闻此讯元七滞愣良久后掩面落泪。陆闻安看得心疼,将她揽入怀中。
马儿踏碎初雪入镇,陆正节下轿瞧见元七时竟然释笑。他道:“安儿书信中道邻户一家已经离镇。房屋空缺,你与袁祯搬进去罢。”
元七惊睁双目,轿帘被手杖挑开,袁祯倾腰唤她:“阿姐。”
一切来得突然,她反应不及,又惊又喜吐不出字。陆闻安深笑一声,赶几人归家。“饭菜该凉了,回去再慢慢道来。”
趁陆闻安为元七拭泪,袁祯对陆老爷深鞠一躬。
原来陆正节与袁将军自幼相识,袁家出事后他并未申冤,而是假意与何守承交好。重建承露台时他私自使用袁将军当初所用石料,历经多年承露台亦完好如初,圣上大喜。他以为时机已到,故在圣上问及石料时和盘托出,熟料圣上忌惮何守承竟将他贬谪。
若非何守承自大,为震慑他擅自邀他回京参宴,惹怒圣上让其找到机会,他也没办法扳倒他。
而所谓病故,其实是死于袁祯之手,圣上为表歉疚未治其罪,欲正他姐弟身份却被拒绝。事到如今,他未死,阿姐也有久伴之人,足矣。
作者前言:
陆闻安问元七是一直记得自己,还是重逢之后才记起来的,元七的回答是:从未忘记。她救下元七是场意外,两次重逢也是意外。不经意逢于意外之间,涟漪难平,所以陆闻安愿意为她离经叛道,为她搏得名分;所以元七愿意为她放弃仇恨,和她安于乡野。
于她们而言情深必寿,愿所有有情人亦然。
——秃头月亮
酒馆编辑后记:这篇故事中元七的勇敢,善良的性格将她的情绪和人格融合在一起,从言语动作和情感中能感受到她的个人魅力,整篇故事交代连贯,用词准确,表达的意象也能够彰显出古风的气息。
——酒馆审编
柠檬味小鲸
你们好我是秃头月亮喜欢写文的在读理工科女一只在秃头的路上狂奔不止爱好瞎写+瞎看很高兴认识你们第篇故事
古言故事
文章有时会同步更新到荔枝FM电台
欢迎收听